




梅梓祥导读:
父亲节那天,陈慧玲战友让我发一张父亲的照片,她制作一个“父亲”专题的视频,我未能满足她。我现在也不想、也不愿接受几十年前的一个事实。
我拜访汪曾祺先生,汪先生问起我的家庭,我说:“母亲……父亲不在了,还有四个弟弟。”空气瞬时凝固,我、汪先生沉默许久。
我用“不在了”替代中国人都忌讳的那个“字”。
杨妙娜的《回忆许军医》写许军医因车祸身亡,全文除一处介绍车祸结果“一女医生当场死亡”外,都用“没”等字所代替(引号系我所加),列举如下:
大家全都知道了许军医人“已去”;;
车上坐的许军医当时就“没了”;
那两个“没了”妈妈的女儿时;
我们朝夕相处的战友许军医怎么就这样“没了”;
“失去”前后宿舍住、天天见面的战友时那透彻心扉的凉……
这是一颗善良、柔软、充满爱的心,不经意地规避那个像刀刃一样锋利的字眼。
文章回忆几位战友陪伴张军医乘车数百公里到车祸现场,探望已故的许军医。许军医、张军医是大学同学,在部队结婚,伉俪情深。许军医在上海生第二个孩子,休完产假返回青藏铁路途中惨遭不幸。在去往车祸现场的车上,战友们小心翼翼向张军医隐瞒实情,以打扑克冲谈“悲痛”的心情。所有的言谈举止,都是对许军医、张军医的战友深情。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一文中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正是。
虽然没有看到过统计,但按常理推想,在偏远地区,交通落后、路况差,车祸的概率应该高过交通发达的地方。铁道兵担负的工程任务又常常在远离都市的穷乡僻壤,从这方面看,铁道兵即便像车祸之类的事故,也是一种牺牲,具有“英雄”的精神。热心铁道兵史研究的王民立战友论述铁道兵部队病故的官兵,有很多患者是因为施工地点距离大医院远,难以得到及时救治而亡,他们应当是“烈士”。云南一位铁道兵老前辈杨德新创造了一个词“隐性牺牲”,认为铁道兵打隧道,有的牺牲在现场,是显现的牺牲,更多的人因打隧道吸入大量粉尘,退伍回乡多年后矽肺病始发,或早逝,或病痛相伴一生。他们对铁道兵有很深的感情,才有这些“合情合理”的观点,我从内心认可并敬重。
许军医修建青藏铁路,救治了许多铁道兵战友,自己却惨遭劫难,留下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我称她为“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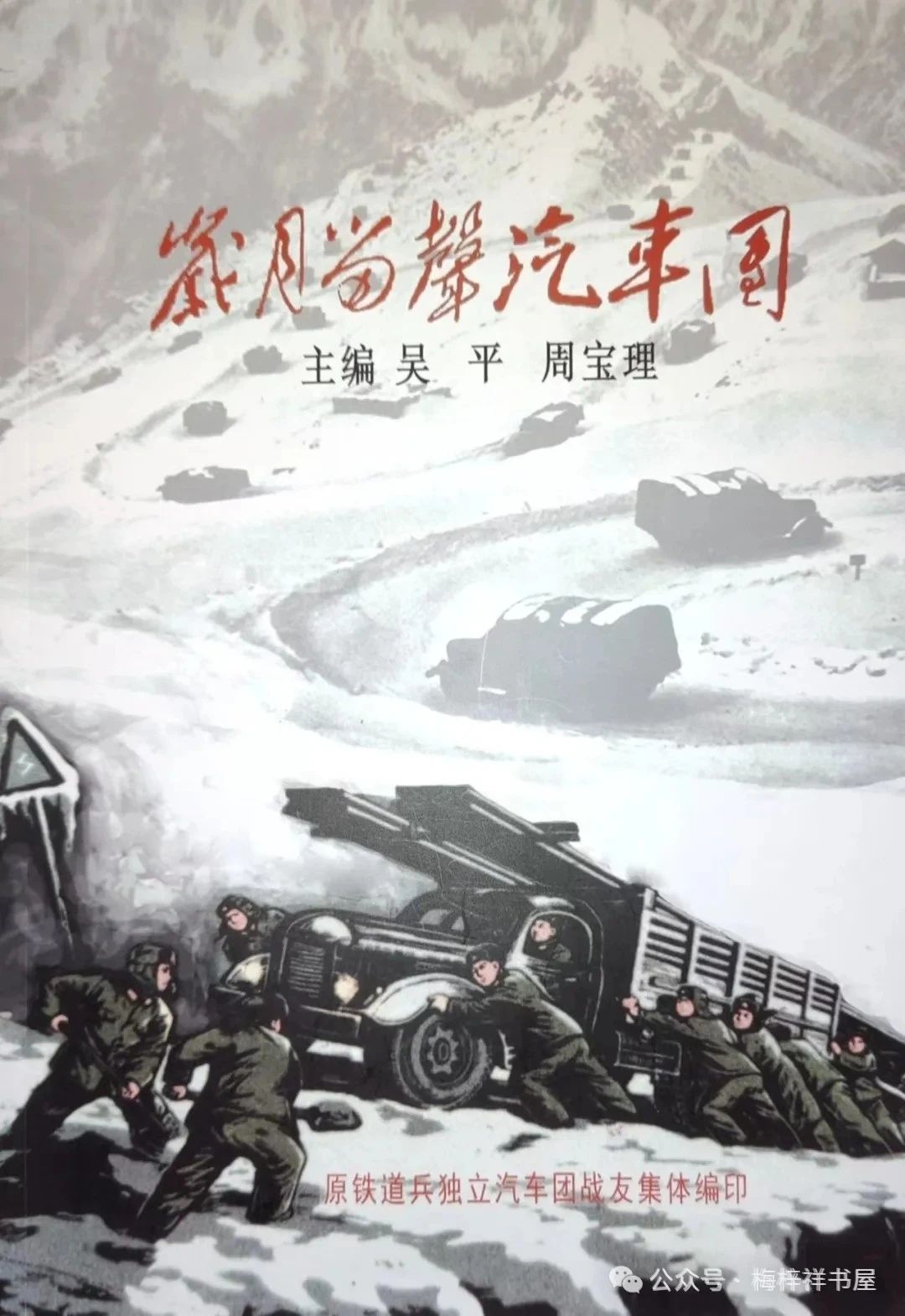
回忆许军医
——谨以此文献给为青藏铁路献身的战友们。
杨妙娜
放假几天出游在外,返回车上细翻群里那些回忆战友,回忆青海经历的文章,不由勾起我对深藏心中几十年,终身难忘的一段往事的回忆。
在青海格尔木七师医院的四年间,曾参与过多次紧急和危重病人的抢救,除了那些年轻战友失血的面孔,永远刻在了脑海中挥之难去外,还有一件往事不但铭心,而且想起痛心并惋惜。
那就是七师医院的女军医许医生。
当年,她在上海休完产假后返回格尔木时,医院的吉普车在出西宁两百多公里处发生了事故。当场,这个刚生了第二个女儿,孩子还在襁褓中的母亲许军医人就没了。
接到后勤通知,医院马上派出救护车,并由副院长领我们五个医护人的小组,加两个司机换着开车,急忙出发赶往现场。最让我心颤抖的是,许军医的爱人、外科的张军医和我们同去。在告知我们任务时,大家全都知道了许军医人已去,院里对张军医编出了善意的谎言,唯有他不知情。记得清清楚楚,我们都上车了只等张军医,因为他五岁多的大女儿刚被他带到格尔木,他要安排女儿来的最晚,不知他冥冥之中有什么预感,来到车前竟没上车,又到处去找人要了一双白线手套带在手上,非常扎眼。车上人心照不宣,谁都不知该怎么面对他,他上车后,见大家只等他,便自言自语说:我女儿在家安排了一下,不过我老婆明天就回来了(实际上医院已对孩子做了安排,第二天派人送孩子去西宁)。听张医生此言,大家惊的不知说什么好,但都故做轻松状,招呼他坐下,即开车奔向西宁方向。
救护车上只有我一个女的,从我接到通知说去参加抢救,并得知医院的小车出了事,车上坐的许军医当时就没了,惊的我脑子突然一片空白,浑身发冷,心中的惊恐让我呆站在那里,被人猛的一戳才赶快跑回宿舍。慌忙中不知该拿什么,背起了军用书包,里边只放了缸子,毛巾就跑到院部。因还没吃中午饭,炊事班用一个笼布给我们包了一大堆热馒头和一小铝盆的咸菜,上车我坐到了最后,坐定开始吃饭,张军医坐在我对面,我完全不敢抬头看张医生,甚至不敢直视他的眼睛,馒头如同石头只觉得噎的难以下咽。这时他还浑然不知永远失去了和他相依相伴的妻子,还不知他那才几个月大,还嗷嗷待哺的小女儿和五岁多的大女儿已经永远失去了母亲。其他的几位和他一起吃了这顿只有馒头咸菜的午饭。我本来刚到饭堂,还没打到饭就被叫了出来,原本肚子饿的咕咕叫,但一听此事,紧张的完全没了饥饿感,这馒头怎么都咽不进去?吃过饭,当时的副所长看着大家谁都不说话,个个都一脸的不自然,生怕露出什么破绽,让张军医生疑。为分散注意力,便从司机那要来扑克牌说:大家玩会牌吧,他们几人在救护车中间放上急救箱玩了起来。大家痛失相处多年的战友,心里装着这当时如同天大,又不能告诉当事人的秘密,内心都痛的沉甸甸,气氛怪怪的,尽管玩着牌但话都不多。因为当时告诉张军医是汽车营的车出了事故,所以只有他一个人此时心里还轻松着。我坐在后面看着此时还轻松玩牌的张军医,想着马上将要面对突降的不幸和痛苦,和那两个没了妈妈的女儿时,不由得要流泪,有人看出我的表情,不断的用眼神示意我。强忍泪水,故作镇定是当时对我们最恰当的形容。
天黑时我们到了乌兰,和后勤王副部长的车汇合了,在大家吃饭时,王副部长让人分别把我们叫出去通告了情况。我们朝夕相处的战友许军医怎么就这样没了,真让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想当时再好的演员也演不下去了。张医生从大家的神情中看出了什么,他突然心生疑虑的说,连副部长都出动了、事故肯定不小,一再追问到底哪的车、几个人,我们都不敢回答。王副部长只能一点点告诉他,好让他有个思想准备,说是医院的车,人只是受伤了。这时的张军医神情一下紧张起来,心仿佛提到嗓子眼儿,急切的问到:伤的如何、伤在哪里?王副部长只说都送医院抢救了。张医生放下筷子一声不吭,饭再也没法吃了。王副部长交代注意安全后,大家分别上车继续出发。这时的张军医没了刚才的只是去完成一项救治任务,履行医生职责的信心和心情,我们车上的气氛可想而知,静的让人无法忍受,张军医难掩内心的恐慌、担心、悲痛抱着头一直爬在车中间的急救箱上,我们的心情也无法平静。
接下来的几百公里和那几个小时,是我这辈子走过的最难、最煎熬的路程,那种五味杂陈复杂的内心感受至今都无法用言语准确表达,真如同炼獄一般。两顿都吃不下饭,加上又惊又怕,从没这种体验的我,不知当时是个什么神情。在乌兰上车时,王副部长看到我瑟瑟发抖,让人给我找了件军大衣穿上,实际这会儿冷的不只是身体,还有那不能言传,失去前后宿舍住、天天见面的战友时那透彻心扉的凉。
漆黑的夜晚,呼呼的风声,只有两束车灯的光柱射向前方,救护车跟在王副部长的车后向西宁方向飞驰,车内除了发动的响声,再无一点动静,谁都不知该说什么。此刻,对于一个将要面临生离死别的人来说,任何安慰都是苍白无力的。对于军队只是痛失了一个女兵,对于张军医失去的是他当时的整个精神世界,他的半边天塌了;对于两个孩子更残忍,失去了陪伴,庇护她们成长的摇篮——母亲。我们每个人都如同一座雕塑,连呼吸都变的小心翼翼,生怕惊扰爬在急救箱上的张军医,就这样大家沉浸在悲痛中一路无语。在凌晨近四点时,眼看着车灯照亮的里程碑上的公里数,距离那出事的地点越来越近,这时车里的空气就像瞬间凝固般让人窒息,所有的人都紧张的心跳加速,闭着气息,但加速的心脏像要跳出来,咚咚声仿佛都能听的见,个个紧握拳头,瞪大双眼盯着前方,此刻我怎么也止不住浑身发抖,那上牙下牙,腿肚子不停的打颤。
也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在我们到达现场第一时间进入眼帘的是:一台起重机刚刚吊起的面目全非、车顶已压扁的师医院的吉普车。看到此景,张军医似乎已料到事故的严重性,我们急忙下了车。现场指挥人员上前给王副部长报告时说:事故中四男受伤己送西宁抢救,一女医生当场死亡。听此言,压抑了一路,也许还抱有很大希望的张医生,在这猝不及防的报告打击下彻底崩溃了,突然扑向吊起的汽车,呼天抢地地凄惨地喊出一声声:“我要我的人啊!我要我的人啊!”然后瘫坐在地上。他哪曾料想到,多年的军医生涯,身为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的他,不知抢救过多少病人,挽救过多少生命,可他最亲最爱的人竟连救的机会都没有给人留下。
许军医是他大学同学,毕业后两人一起分到了部队,又都是上海人,在部队两人结了婚,一直都没分开过。许军医治病救人也多年,自己竟走的那么决然,没有留下一句话。随后我们大家连拉带拽搀扶起张军医,我们被带到在离现场不远的一个当时还属保密单位的招待所。所有人都进了一个会议室陪着张医生,身为军人的男儿们也都满脸悲伤,掩面叹息。因只有我一个女的,王副部长就让我出来了,但也没有地方呆,只好到招待所值班室,和两位四五十岁的女值班员呆在一起。房间有个炉子,她俩只有一张床,我坐在炉子旁,耳边不断传来張医生悲痛的哭喊声,不由我泪流满面,两位值班员一直在埋怨说,三更半夜怎么让你一个女的来干什么?我想此时我除了是女的之外,因为我还是个兵啊!就这样坐着,不停地流着泪等到天亮。天亮后,来到这个单位卫生所,用担架将许军医抬上我们救护车,张军医撕心裂肺的哭着、扑着要上救护车,被硬拉上了王副部长的车。救护车上,我们分坐两旁,担架放在我们中间,护送许军医去西宁。这时看着已被我们用床单盖上面部的许军医,没有了当初的惊恐,反而让人感到的是真正的悲伤,想想上一面见她还是活生生的许军医,此刻却阴阳两隔,悲痛的情绪让大家不由的抽泣着。她才不到40岁,还太年轻,她是多么的不忍离去啊,不忍离开两个年幼可爱的女儿,不忍离开挚爱相随的丈夫,还有那未尽的事业和等待她救治的病人啊!然而这一切都己成为不可能,她年轻的生命被定格在一九八零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段经历如同愈合的伤口,一直不忍去触碰。在这雨纷纷,欲断魂,祭英灵,忆战友的季节里,群中战友文,让我想起刘学谦战友那无血的面孔和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青海高原的蓝天白云啊,你一定还记得那些魂断雪域,血洒高原的年轻战士;巍巍昆仑,茫茫天路啊,一定不会忘记那个曾经在此献身的铁道兵女军医……

杨妙娜,1955年1月出生于陕西西安,中共党员,1970年12月入伍,1970年12月至1976年10月铁道兵独立汽车团(警通排电话班),1976年10月至1980年12月铁道兵第七师医院,1980年12月至2010年空军试飞团、空军航空兵第23师、空军航空兵第45师等单位工作。
照片由作者提供
(本版编辑: 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