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小时候喂鸡那些事儿》,想起法布尔的《昆虫记》。昆虫与家禽的世界,如此神奇、有趣而迷人。
鸡屁股是家庭“储蓄所”,捉蚂蚱喂鸡,母鸡孵小鸡的恋窝,小母鸡初次下蛋找窝的焦躁,奶奶挑鸡娃的经验,五个爪的大红公鸡……无不引人入胜。
真羡慕作者有一个丰富多彩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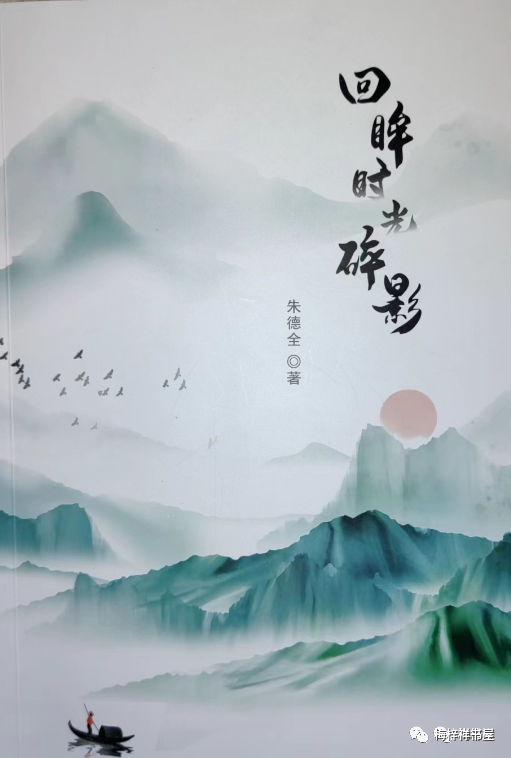
小时候喂鸡那些事儿
朱德全
前几天,网上传言鸡蛋涨价了,说鸡蛋涨价快,快成“火箭弹”了。家里的鸡蛋不多了,我和老伴一起去超市买鸡蛋,发现鸡蛋真的涨价了,普通鸡蛋七块多钱一斤,散养的“柴鸡蛋”竟要十几块钱一斤。
鸡蛋价格受市场多种因素影响,随着粮食、饲料、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而水涨船高。
买鸡蛋让我想起了童年时养鸡的那些事儿。我是在农村生活长大的,小的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养鸡养猪,家乡话叫喂鸡喂猪。
我小的时候,农村还没有脱贫,靠种地为生的庄稼人,除了精耕细作,盼望地里多打粮食外,家里还要喂鸡喂猪,想办法弄几个零花钱。
有人把鸡屁股比作家里的“储蓄所”,可以零存零取。鸡下蛋,蛋变钱,也可以直接拿鸡蛋到村里的供销社换油盐酱醋和针头线脑。那时候鸡蛋不论斤卖,论个卖,一个鸡蛋5分钱,可以换半斤食盐或2两酱油。
家庭喂猪的好处多,猪好比是活着的“造大粪机器”,吃的是生活打下的厨余垃圾,拉出来的是有机肥料。家养一头猪,平日里生活的刷锅水、剩饭剩菜、皮皮糠糠、打下的菜叶菜帮,都有了去处。喂猪可以积攒农家肥,猪喂肥了可以卖钱。如果说喂鸡是“零存零取”,那么喂猪就是“零存整取”。
妈妈和奶奶对喂鸡喂猪特别操心,无论多么忙,家里都要保持喂一头猪、喂十来只下蛋的鸡。而且每年都要添小鸡,延续不断。猪快要出栏了,先买个小猪仔搭拉着,大猪卖了,小猪“接班”。
从我记事起,就在妈妈奶奶的吩咐下,做些喂鸡喂猪的事儿。放学回家,趁天还没黑,拿着镰刀、背着箩头筐到地里割猪草,或者是到大堤上去捉蚂蚱来喂小鸡。每天早上,帮妈妈和奶奶抽开挡鸡窝门的砖头,把鸡放出来,让鸡出来觅食,到了傍黑,鸡回家了,数一数都上窝了,把鸡窝门用砖头堵上,防止夜间黄鼠狼、狐狸来偷鸡。
经常参加这些家庭劳动让我从小养成了爱劳动的习惯,也给童年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回想起小时候喂鸡的那些事儿,特别有趣。
过去家庭喂鸡都是散养,鸡在庭院里和家附近随便溜达觅食,捉小虫子、吃草籽和其它食物。按现在人们的说法,这种鸡叫“溜达鸡”“土鸡”或“笨鸡”,下的鸡蛋叫“土鸡蛋”“柴鸡蛋”。
散养的鸡基本不用喂食,有时候遇到下雪天、下雨天,或者下蛋的时候多少给加点餐。鸡吃的食主要是打下的白菜帮或菜叶子剁碎拌些麦麸,或者给撒些玉米粒。没有长大的小鸡娃需要特殊照顾,喂些小米之类的“细粮”。奶奶说,小鸡爱吃蚂蚱,吃蚂蚱小鸡长得快,长得壮。我经常到沁河大堤上去捉蚂蚱来喂小鸡。
春夏时分,大堤上的草丛中有不少蚂蚱和叫狗(蛐蛐),一会儿功夫能捉不少。我用狗尾巴草把捉到的蚂蚱、叫狗串起来提回家,大鸡小鸡看见我手里的蚂蚱,都跑过来围着我,小鸡“唧唧”叫,大鸡飞起来从我手里抢蚂蚱吃。我把蚂蚱串举得高高的,逗小鸡玩,扔下一个蚂蚱,一群鸡一起去抢,抢到的叼着蚂蚱就跑,没抢到的在后边追,可开心了。
家里喂的鸡不是一个品种,有大有小,有老有少,鸡的颜色也不一样,有黑鸡、白鸡、黄鸡、花鸡等。在奶奶的口中,鸡的颜色就是鸡的名字:大黄鸡、小黑鸡、花母鸡、小白鸡、红公鸡、芦花鸡等。鸡好像能听懂人的声音,喂鸡的时候,奶奶“叼叼叼”的一叫,家里的鸡立马都跑过来了。
家里只要保持十来只下蛋的鸡,基本上就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零花钱。下蛋的旺季,每天可以捡五六个鸡蛋,买油盐、打酱油打醋、买火柴煤油的钱就有了。靠抠鸡屁股过日子的庄稼人,天天盼着家里的鸡多下蛋。但家里过日子俭省,自己很少吃鸡蛋,大部分用来卖钱,或者拿到供销社换油盐酱醋。另外,农村的人情往来多,走亲戚、看病人、瞧月子都要拿鸡蛋。
那时候家里繁衍鸡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老母鸡孵小鸡;一种是买鸡娃回来养。
解放初期,家乡的农村还没有孵小鸡的作坊,每年家里都让老母鸡孵一窝小鸡。奶奶有经验,发现有的老母鸡不下蛋了,身上发热,焦躁不安,恋窝不出来,那就是想要孵小鸡了。奶奶马上给它垒个窝,垫些麦秸和干草,放十来个鸡蛋,把母鸡安放在窝里让它孵。农谚曰:“鸡鸡,二十一,鸭鸭,二十八”。鸡蛋经过21天的孵化,小鸡娃破壳而出,十来个鸡蛋一般能孵出八九只小鸡娃。我问奶奶为啥不多放点。奶奶说:放多了,母鸡的翅膀裹不住,容易不出苗,孵出的小鸡多了,母鸡也带不过来。”
春天孵的小母鸡一般养到第二年春天才嬎(念fan,下的意思)蛋。小母鸡第一次嬎蛋,不知道嬎哪里,焦躁不安,一会儿飞到窗沿上,一会儿钻到旮旯的地方,不停地扒高上低,飞来飞去。奶奶看见了,知道它要嬎蛋了,吩咐我把它逮住,摸摸屁股里有没有鸡蛋。如果有鸡蛋了,就用砖头垒个窝,或者找个竹筐,里边放些麦秸,把母鸡放在里边,用东西盖住,逼它在里边嬎蛋,防止它到处跑嬎“野蛋”。母鸡有记忆,第一次在这个窝里嬎蛋,以后它总在这个窝里嬎蛋。“咯咯哒,咯咯哒”,“下蛋了,下蛋了”,母鸡下完蛋都会用叫声来“报功”。奶奶听见了,一般会给它撒几粒玉米作为“奖赏”,并催我快去窝里拾鸡蛋。奶奶对我说:“鸡刚嬎的蛋是热的,放在眼上暖暖眼,眼睛明亮不害眼。”我相信奶奶的话,每次听到“咯咯哒”的叫声,立即跑去拾鸡蛋,热乎乎的鸡蛋放在两个眼上暖一暖,很舒服。
吃“大食堂”饭那年,家庭不让养鸡了,鸡也改吃“大锅饭”了,生产队在我家不远的小瓦窑办了个集体养鸡场。我常去鸡场玩,鸡场的鸡太多了,成千上万只,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以哨音为号。饲养员的哨音一响,所有的鸡连飞带跳从四面八方围到饲养员身边等着喂食。我觉得好玩,但奶奶却不高兴,说家里不养鸡,连个零花钱都没地方弄。
不久,大食堂解散了,生产队的养鸡场也散了,鸡又回家了。后来,农村有了孵小鸡的作坊。到了春天,每天都有卖鸡娃的货郎挑着两个竹菠萝,簸箩里装满了小鸡,走街串巷喊叫着“鸡娃、鸡娃”的叫卖声。每只小鸡两毛钱,买多了还有送。买小鸡娃养比老母鸡孵小鸡省心多了。奶奶不再用老母鸡孵小鸡了,都买小鸡娃回来喂。
奶奶挑鸡娃有经验,拿起一个小鸡娃,先看它拉没拉稀,摸摸屁股有没有硬疙瘩。奶奶说,屁股有硬疙瘩的鸡娃发育不好,拉稀的鸡娃有毛病不容易养活。接着,她把鸡娃放在手中,轻轻颠一颠,看它的反应,反应机灵的,叫声清脆的、翅膀硬的鸡娃容易成活;然后看鸡冠,鸡冠大的、发红的可能是公鸡。小鸡娃买回家,要享受一段特殊待遇,奶奶把它们放在一个篮子里,里边放旧棉花套,每天定时喂食,放出来它们在地上跑一会儿。晚上让它们呆在篮子里挂起来,上面盖毛巾或篦子,防止老鼠和蛇侵害,也防止它们跳出来摔死。
家里喜欢喂母鸡,不喜欢喂公鸡,母鸡养大了下蛋,喂公鸡不划算。一个家庭的鸡群中一般只保留一只公鸡,让它压蛋,当“鸡头”,护母鸡。待小鸡娃长到一捧大的时候就能分出公鸡母鸡了,小公鸡一般不保留,卖掉或者杀吃了。

高傲的 大红公鸡
我家养的鸡群里一般只有一只大公鸡,其余全是母鸡。奶奶说,有个公鸡,母鸡爱下蛋,邻居家的公鸡不敢来捣乱,公鸡多了老打架,不好。那时候家里没有钟表,靠听公鸡叫和看日影来掌握时间。公鸡叫的时间很准,每天凌晨,公鸡“咯咯喔”地叫, 鸡叫第三遍,我该起床上学了。到了晌午边,公鸡“咯咯喔”又叫了,妈妈听到公鸡叫,开始做午饭了。鸡还可以预报天气,头天晚上鸡犹犹豫豫、迟迟上窝,第二天不是阴天就是雨雪天,很准。
我家曾养过一只大红公鸡,我特别喜欢它。它长得很帅,雄健、威风,特别漂亮,与图中的公鸡一模一样。大红的鸡冠,鲜红明亮,像戴了一顶漂亮的“皇冠”,脖子周围一圈金黄色的羽毛,像围了一条金色的大围脖,尾巴高高翘起,深色的羽毛,闪着绿光,像竖起来的一面旗帜。家里的母鸡都围着它转。“红公鸡,绿尾巴,尖尖嘴,四个爪”,像小时候唱的儿歌那样。鸡有四个爪,可我家的大红公鸡有五个爪,小腿上多长出一个爪,怪不得它那么厉害。这个大公鸡是名副其实的“战斗鸡”,邻居家的公鸡都打不过它。它经常昂着头,一副高傲的样子,有时候它金鸡独立,有时候左顾右盼,守护着自己的“后宫”。有它在,邻居家的公鸡不敢到我们家来“串门”,外边的母鸡来了,肯定要被它强迫压蛋。有一次,我看见它与邻居家的公鸡打架,两只鸡怒目圆睁,脖子上的毛全支棱着,跳得老高攻击对方。没有几个会合,邻居家的公鸡就败下阵来,落荒而逃。后来,因为“传鸡”(鸡瘟),村里的鸡都死了,这只大红公鸡也未能幸免。鸡死了,姐姐用它脖子上的鸡毛做了两个漂亮的毽子。奶奶说,这样好看的鸡毛做成鸡毛掸子最好,就是一个鸡的鸡毛太少了,做不了一个鸡毛掸。
我的家住在村庄边上,鸡有时候会跑到庄稼地里吃东西。有一次,三只母鸡吃了田里拌农药的麦种子,中毒了,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奶奶看见了,赶紧吩咐我抓把绿豆捣碎,用绿豆水往鸡嘴里灌,有两只没有救过来,还有一只大黄鸡坚强,奶奶见灌绿豆水不行,立即拿来剪刀,在火上烧一烧消消毒,然后豁开鸡嗉,把里边的食全抠出来,然后用绿豆水冲洗鸡嗉,冲洗完后用缝衣服的针把鸡嗉缝起来,这只鸡居然被救活了。
现在,科技发展,乡村振兴,农村养鸡也实现了现代化,养鸡场大规模养鸡,很少有家庭喂鸡了。去年我回老家,转了几个村庄,发现只有一家养鸡的,是用网围起来养。经打听才知道这家是开农家乐饭店的,养的鸡叫“土鸡”。客人来吃饭时可以现场点,现点现杀,一百元一只。现在,农民富了,靠抠鸡屁股过日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本版编辑: 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