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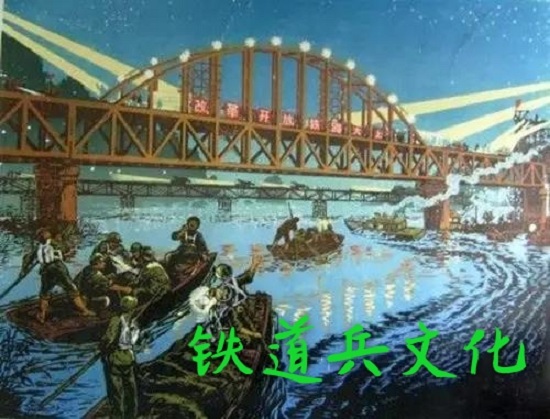
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大武汉的新鲜事,惹得我一直怀揣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去到那里,亲眼看一看它的热闹与新奇。尽管家乡嘉鱼县离武汉不过几十公里,但因为那时交通不便,去武汉(我们那里的人叫“下汉口”)唯一的途径是坐长江客轮,又贵又慢,所以梦想一直没能实现。
16岁时我要去地区所在地孝感上学,必须路过武汉,这才第一次圆了我的梦。此后的经历就是上学、参军,往来武汉成了家常便饭,成年后成了武汉的女婿,武汉对于我不再神秘。
然而,因为熟悉反而生疏,因为亲近反而忽视。正像苏轼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几十年过去了,我在武汉或来来往往,或长住久留,对那里的许多事物反而熟视无睹,如今才发现自己对武汉竟然还是不甚了了。
在中国,只有两个城市被称作“大”:一个是大上海,一个是大武汉。上海之大自不待言,而武汉凭什么称“大”?原来也是有道理的。
首先是它地盘大,武汉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汉水在这里汇入长江,市区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湖泊,人称“大江大湖大武汉”。长江从武汉穿城而过,市区范围的江面上光长江大桥就修建了11座。武汉的面积达8500平方公里。做个形象的比较吧,一个武汉的面积相当于4个东京、8个香港、12个新加坡、80个巴黎,是上海的1.34倍,南京的1.29倍,广州的1.14倍,约等于厦门+深圳+香港三座城市之和的2倍。你说大还是不大?
当然,武汉之“大”并不仅仅体现在它的面积上,其人口规模、经济体量等,也都是个“大块头”。而从深层次上讲,武汉称“大”还在于它所具备的大格局、大胸怀、大气魄、大容量特质。

武汉是近现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它是一座移民城市,居民来自四面八方,这就决定了武汉人有一副开放的胸襟。号称“天下第一街”的汉正街,就是武汉海纳百川的一个缩影。汉正街位于汉口,附近的长江从西至东有众多码头,这是近现代商埠吞吐、物资集散之地。经年累月,本省各地和外地各省人口纷纷迁入开设店铺,沿街的店铺行栈日益增多,贸易往来渐趋频繁。到清代康熙、乾隆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汉正街已成为“汉口之正街”。这个被称为“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唯意”的地方,吸引了四方商旅,八方游客,热闹繁华,盛极一时。
说起大武汉的发展,就不得不提晚清名臣张之洞。张之洞督鄂18年,在湖广大地大力推行洋务新政,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开创了一系列耸动中外视听的早期现代化事业,使武汉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由一个商业大都会,转变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教育、文化的国际化大都市。
“大武汉”本非武汉人的自称。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里说:“要把武汉建成纽约、伦敦之大,要建设成东方的芝加哥”。辛亥首义成功,中山先生称“武汉一呼,四方响应”。武汉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大革命时期,武汉曾经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又一度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当时有一首响彻全国的歌,歌名就叫《保卫大武汉》。歌中唱道:“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我们要坚决保卫她,像西班牙保卫马德里”,“用我们无穷的威力,保卫大武汉”。
1954年,武汉遭遇特大洪水,长江沿线乃至全国都响起了“保卫大武汉”的口号,鼓舞千万中华儿女与长江大堤共存亡。1998年长江沿线再次遭遇洪灾,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武汉,又一次提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保卫大武汉”。

以上所述事实,说明大武汉的声名由来已久。但惭愧的是,我对于武汉之大的印记,却还停留在影影绰绰似是而非的层面,要说出个子丑寅卯还真不行。
2023年春节,是三年疫情过后的第一个轻松畅快的春节,人们压抑了许久的心情得以舒缓。许多人迫不及待地放飞自我,外出旅游,投入到所谓“报复性消费”的洪流之中,四处购物。我消费的能力不足,兴趣也不浓,便利用回到武汉过春节的机会,抽空来了一个“报复性参观”,用自己的脚和眼睛认真感受一下武汉之“大”,正好补一补对武汉认识不足这一课。
开始时只是信马由缰,后来发现了一个现象:在旅游地图上,武汉三镇许多地方都用红五星作了标记,原来这些都是红色革命纪念地。其中有一些地方我过去零零散散地逛过,但印象不深了;更多的地方却从未涉足。这些被标出的红色纪念地主要围绕着辛亥首义、二七罢工、北伐战争、国民革命、抗日战争、武汉解放等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最突出、最闪光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革命活动纪念地。有中共五大会址、党的八七会议会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毛泽东同志旧居、陈谭秋烈士纪念馆、中共中央宣传部旧址和瞿秋白旧居、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和刘少奇旧居、中共长江局旧址和罗亦农旧居、向警予烈士陵园、红色战士公墓等。由于受时间、精力限制,要想挨个看一遍显然力不从心,于是就选择了其中一些作为目的地。
这次目的明确的参观收获确实不小,学而后知不足,我真切地感觉到自己过去对武汉红色革命历史了解得太少了。
“全世界都知道,1927年的汉口是‘红色的汉口’”,这是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中写的一句话。确实,1927年初,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中国革命的中心就在武汉。
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中国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国共两党有智慧和远见的政治家们,开始瞩目武汉这座长江中游、连接南北、九省通衢的战略要地,敏锐地感受到革命重心必须北移,以推动中国革命向全国发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逐渐成为大势所趋,政治所向,众望所归。
1926年1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迁都武汉的原则决定,随后派遣一批大政要员启程北上,筹备迁都事宜。1927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宣布国民政府正式开始在汉口办公,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
中国共产党也吹响了向武汉集结的号令。1926年9月,张国焘以中央驻汉代表身份首先前往武汉,指导发展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负责与国民党党、政、军合作沟通,多次呼吁中共中央尽快迁至武汉。随后,中共中央又调项英、李立三、毛泽东、刘少奇、罗章龙、吴玉章、张太雷、恽代英等人抵汉,党在武汉的力量迅速聚集。1926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在汉口成立中共中央汉口临时委员会,全面负责武汉方面的各项事务。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机关也陆续向武汉集结。中共中央军事部汉口办事处是最早迁移武汉的中央机关办事机构,此后中共中央农委、工委、宣传部、组织部、妇女部等陆续迁来武汉。1927年4月中旬,陈独秀抵汉,中共中央最后一个机关中共中央秘书厅也迁入武汉。至此,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迁到武汉,党的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绝大多数都已到达。
党中央进驻武汉后,工农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当时刘少奇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和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他深入工人斗争第一线,积蓄斗争思想方法,撰写了《工人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三本小册子,成为指导工人运动的宝贵文献。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通过32天在湖南农村的考察,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回击了部分人对农民运动的责难,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瞿秋白称他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王”。
革命中心转移武汉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武汉更是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最残暴的地区之一。
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这样才能挽救革命。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按图索骥地找到了位于武昌都府堤20号的中共五大会议会址。这里当年是湖北省立第一小学,前身是1918年创立的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谭秋早年在该校担任英语教师,新中国著名外交家伍修权那时就是他的学生。陈谭秋在学校传播革命思想,从事革命活动,因此,现在这里同时又是陈谭秋烈士纪念馆所在地。

中共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等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人也出席了大会,国民党领导汪精卫、徐谦等列席了会议。
中共五大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会议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但并未得到很好的纠正。
中共五大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是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我党历史上首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监察委员会由10人组成,王荷波为主席,杨匏安为副主席。10人中有8人分别来自8个地区,在不同地区担任过区委(即省委)书记、区委委员、区委候补委员,革命斗争经验丰富,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为了纪念党的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更是为了宣传和传承我党纪律监察的光荣传统,促进党的廉政建设,如今在都府堤红色一条街中共五大会址附近,建起了两处与党的纪律监察相关的设施。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这是在中央纪委和湖北省委指导下,武汉市委用3年时间建成的廉政建设专题展览馆。陈列馆展出场地有三层,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展出了文物资料400多件套,珍贵历史图片700余幅。我在这里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才看完这个展览。另一个设施是“武昌廉政文化公园”,公园里有一尊巨大的群雕,再现了中共五大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英姿。园里有多座石碑,刻着党的领袖人物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名言。公园里最重要的建筑是一条环形长廊,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展厅,悬挂的图片记录着近百年来党纪与廉政建设的大事。文化公园里,有人在参观,有人在休息聊天,有人在锻炼,有人在唱歌跳舞,历史与现实融汇在同一个空间里,革命前辈艰苦卓绝的斗争与今天人民的辛福生活隔空对照,让人浮想联翩。
就在我马不停蹄的参观革命纪念地时,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个朋友给我发来微信,说他们正在排演一部反映八七会议史实的话剧《狂澜》,希望我能去观看并提意见。我对八七会议的情况只知道一些皮毛,不敢贸然前往观看,更谈不上提意见。于是决定先去参观八七会议会址,补补课。

八七会议会址在汉口原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当年这里是俄租界,周围还有英、法、德、日和比利时的租界。如今这里处于一片繁华街区之中,汉口江滩、吉庆街商业区、黎黄陂路历史文化风貌街等,环绕四周。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召开的背景是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于1927年8月7日召开的这次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只是一次紧急会议,通常称为“八七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消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会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由于情况紧急,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但它所取得的成果是重大的,其意义和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为了纪念这个重大事件,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不忘初心,踔厉奋进,依托会议旧址,建立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纪念馆馆舍共3层,建筑是1920年英国人建造的一排西式公寓的一部分。纪念馆由基本陈列展厅、辅助陈列室、临时展厅、复原会场和办公用房构成,于1978年8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邓小平、李维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来馆视察,邓小平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纪念馆现已成为武汉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82年,国务院公布会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中宣部命名纪念馆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我在参观过程中发现,游客中有一些来自全国各地,有的还是外国游客,说明人们对党的这段历史还是非常关注的,这让我甚是欣慰。
为进一步领会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主张,我去武昌拜谒了毛泽东旧居,并再一次参观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倡议并创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7年3月7日开学,4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时间早于八七会议数月。首批800多名青年学子怀着革命激情,从大江南北汇聚到武昌蛇山脚下,听革命导师们讲授革命道理,共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流连于农讲所的教室、宿舍、食堂、教研室中间,我仿佛置身于当年的时空,真切地感受到一群热血澎湃的革命青年为救国救民所表现出的学习热情和斗争精神。
农讲所由毛泽东主持,而且亲自授课,他是讲课最多的老师。此外,授课老师还有瞿秋白、恽代英、彭湃、方志敏等一批学识渊博、革命经验丰富的共产党人。
离农讲所大约300米的武昌都府堤41号,就是毛泽东旧居,同时也是中共中央农委所在地。走进大门,堂屋左边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工作室兼卧室。房间设施简单,只有一张木板床铺、一张书桌,书桌上放着笔、砚、文稿和一盏煤油灯。令人惊叹和敬佩的是,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房间写成的。
当时,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却遭到了一些人的怀疑和责难。农民运动到底好不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27年1月,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身,历时32天,行程700多公里,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进行了实地考察。毛泽东广泛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2月12日他回到武汉,写下了这篇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当时毛泽东白天在外奔波,只能用晚上时间写作。为了使毛泽东有充沛精力运筹革命大事,身怀六甲的杨开慧她夜以继日对农运调查材料进行分类、选择、综合,还帮忙誊写抄校。正是在杨开慧的全力配合下,仅用4天时间,毛泽东就完成了这篇重要著作。
时年28岁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都府堤毛泽东旧居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据点,蔡和森、彭湃、郭亮、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罗哲等共产党人都先后在这里居住过。这里也是毛泽东温暖的家,他与杨开慧母子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得的温馨的家庭生活。1927年4月4日,正是农讲所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杨开慧和毛泽东的第三个孩子毛岸龙在这里出生。虽然近在咫尺,可是毛泽东第三天才在百忙中抽时间到医院看望妻子和儿子。毛泽东走进病房就说:“3天了,我都没来看望你,真对不起! ”
随着武汉革命形势日趋恶劣,6月中旬,毛泽东安排杨开慧带3个孩子回到长沙。之后,毛泽东就踏上了领导秋收起义,带领队伍上井冈山的征程。1930年,杨开慧在长沙被捕牺牲。武汉是毛泽东、杨开慧一家最后团聚的地方。
武汉对于毛泽东而言,既是他生命中最柔软的情感之所系,也是他革命思想逐渐成熟之所在。他在这里提出了诸多革命主张,不仅极大的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也为塑造他革命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革命年代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与武汉结下了不解之缘。青少年时期,他8次到武汉,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48次到武汉,少则三五天,长则十天半月,最长的一次住了178天。从1956年到1966年十年间,毛泽东在武汉18次畅游长江。
毛泽东在武汉留下了许多文墨之宝,其中有为《长江日报》题写的报头,为武汉大学题写的校名,东湖磨山离骚碑上刻着他用颜体书写的屈原《离骚》全文,汉口江滩武汉人民抗洪纪念碑是他题写的碑文,还有为武汉长江大桥落成纪念碑的题字、为江岸二七烈士纪念碑的题字等等。当然,最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当数他分别于大革命时期和解放后在武汉写的两首诗词《菩萨蛮.黄鹤楼》和《水调歌头.游泳》:
菩萨蛮
(1927年春)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水调歌头
(1956年6月)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前一首表现了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他身处危难的环境中,对革命形势产生的深深忧虑,以及澎湃于胸的满腔热血;后一首则是面对祖国日新月异的美好景象,由衷地发出了赞叹,并表达了党决心带领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雄心大志。
大武汉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和百年的沧桑巨变,不仅激起了领袖的无限感慨,也让千万武汉人民心中常怀对党和家乡的热爱。武汉的今天,中国的今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是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奋斗所造就。
春节过去了,我要回京了,但有一个地方必须抽时间去一趟,那就是位于汉阳龟山西麓的向警予烈士陵园和红色战士公墓。

向警予是我党早期的创始人之一,是第一位女中央委员,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杰出领导者。革命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候,向警予在武汉的党中央机关工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血腥屠杀,她不顾个人安危,在中央机关撤离武汉时,主动要求留下来开展工作。由于叛徒的出卖,她不幸被捕,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如今的向警予烈士陵园和向警予烈士生平陈列展,成为无数后来人凭吊她光辉人生的场所,她的事迹在千万人心中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向警予烈士陵园里,还展示着大革命时期在武汉牺牲的48位党的领导人和著名革命者的壮烈事迹。我从头到尾认真观看,反复念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久久不忍离去。与向警予烈士墓园毗邻的,是红色战士公墓,公墓纪念的除上述48位烈士外,还有当年武汉党组织遭破坏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数以千计共产党员、革命志士,他们中的许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参观了这么多革命纪念地以后,我对大武汉的认识得到了一次升华。我深深领悟到,武汉的“大”决不仅仅体现在地域的广阔,人口的众多,经济的发达,声名的远大,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与牺牲,是它在伟大祖国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满载着参观的重大收获,我要离开武汉回北京了。在高铁武汉站,我仰望着庞大的站房,凝视两边平缓,中间凸起,呈现9条楞的巨大屋顶,想起了关于它这般造型的一些传言。有人说这叫“腾飞的九头鸟”;也有人解释说它的寓意是“中部崛起”。我宁可相信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武汉这座现代大都市,九省通衢,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中心,华中地区最大的国家中心城市,今天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踏上了新的征程。肩负时代重任的大武汉,再次腾飞,再次崛起,难道不是正合时宜吗?
2023年4月16日
编辑:兵心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