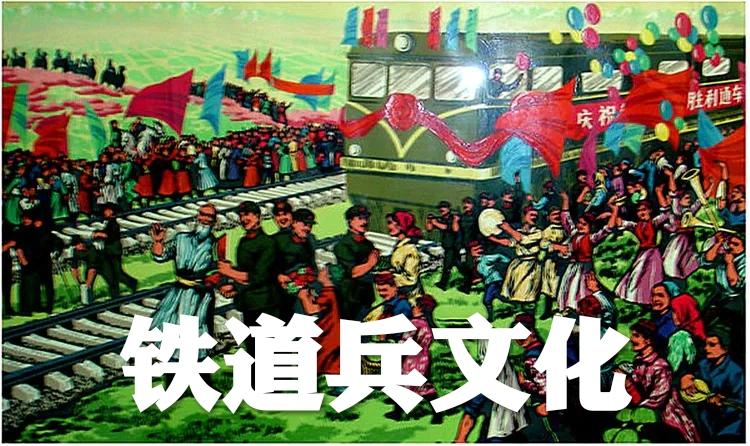铁道兵文苑
初试牛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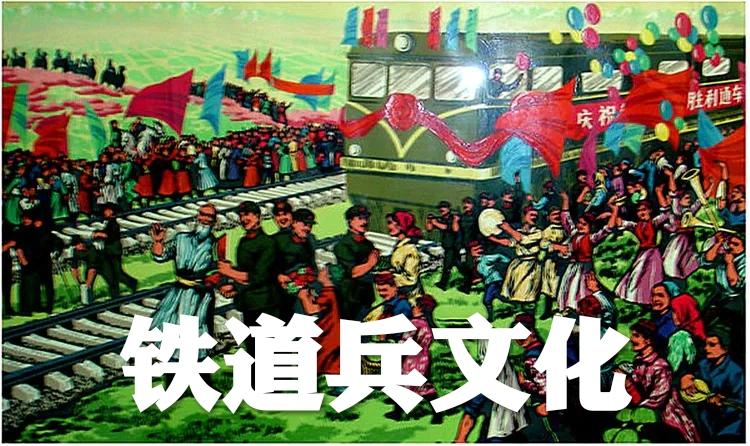
徐总回答得干脆:你若去考学,三年不写稿我都高兴;你若不考学,天天发稿我都不愉快。我是为你将来着想啊!
就是为了让总编高兴,就是为了自己能有一个当好记者的将来,我走向考场。
可贺,居然考上了,且是新闻专业。
两年后毕业,自己感觉浑身是劲,想找一个平台练练功夫。这时,军委办公厅给报社发涵,借调我去吕正操公办室,协助将军整理冀中抗战的文稿。这样,想下新闻海洋摸鱼的想法再次落空。
两年后,我回到人铁。人铁4年,白拿了4年工资,还没正儿八经地干过记者的活儿。这时,常务副总严介生派我去衡广复线采访。此前,人铁已有多位记者前往那里。我去了一个星期,跑了工地,查了当地关于交通的文史,便回京了。
准备下笔时,一位老记者谓我:“此稿你就别参与了,由我和赵中庸来写。”我满口答应。因为我当时正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的确不愿让零零碎碎的事情,中断一部宏大述事的创作。
几天后,严介生副总编打电话找我,让我火速去报社一趟。
在报社二楼的会议室里,有严总,有李丹副总编,有赵中庸,有记者部主任,还有那位执笔的老记者。
严总面色严肃,手里拿着文稿说:“这稿不能用!衡广复线是全路建设的重中之重,举国注目,国内各大报纸派去记者。广东的媒体,把金敬迈,赵寰这两位文学大腕都请去了,给他们的报纸写稿。对于《人民铁道》报来说,这不是挑战也是挑战。我们自己的活,如果干的不如外来人干的漂亮,能说得过去吗?
现在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大战来临的气氛!一种把红旗插上高地的志气,在严总口中飞扬!
他说的金敬迈,是《欧阳海之歌》的作者,其功力不必多述。赵寰1925年生於丹东,是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创作组长、团长。中国文联第三届理事,第四届常务理事。创作剧本有《董存瑞》《南海战歌》《南海长城》《秋收霹雳》《神到风雷》等等。
严总说,这一稿推翻重来,第二稿由朱海燕执笔,后天早晨交稿。
之后,严总对我说,放开写,思想解放一点。
回来后,放下原来的书稿,将衡广复线采访所得在脑子里过滤一遍,提炼出一条思想的光带,于是伏案走笔。
至第二天早晨,文稿完成6000字。这时赵中庸推门而进。他说,找我喝酒,实则是想看看已完成的部分稿子。看完后击掌叹道:“可以,可以,就照此写下去”。一个上午,我与赵主要是交流思想,他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彼此思想相互撞击,使之报道主题更进一步得到深化与提高。中午,我们在永定路延吉冷面馆喝个半醉,之后,他回报社;我回家继续笔耕。
又次日,14000字长篇通讯《留给苍茫大地》完稿。我送至严总手里,他细看一遍,挥笔写下“发排”二字。
此稿见报后,在路内产生巨大影响,报社收到二百多封读者来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
不少人对照各报纸所发文稿,说此稿给他们盖帽了。
文章之所以引起反响,有以下几点,一是引用“布里丹效应”,揭示了铁路多年形成的困境:想让驴拉磨,又不想让驴吃草;让驴吃草,又怕花钱,不花钱,还想让驴拉磨。中国铁路如同“布里丹效应”,想修路,又怕花钱。不修路,还想让铁路满足国民经济上新台阶的要求。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哟!
改开之后,铁路每年增长的运营里程,大至相当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如此这般,铁路怎能不拖国民经济的后腿!这一论点的提出,无疑刺到了社会的痛点,摸到了时代的难点。铁路要上去,政策必须改变,必须增加铁路的建设投资。
其二,大量笔墨,去写建设者的艰难与困苦。隧道局打通大瑶隧道之后,工程处欠下的债务重如泰山,为还债,卖掉了办公楼……
在工地3年未曾探家的职工,退休告老还乡时,想乘坐一次硬卧。副处长四面求人,而末能为自己的职工解决一张卧铺票。
这是个案吗?不是,这是几十年来建设职工所承受的共同的普遍的凄苦的现象啊!修路的,没有铺睡,他们坐着,站着,奔波着,而妻室儿女还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半边户”。
此文发表后,我算在《人民铁道》报小试牛刀。结果不错,此文获1988年铁路新闻一等奖。
(本版编辑: 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