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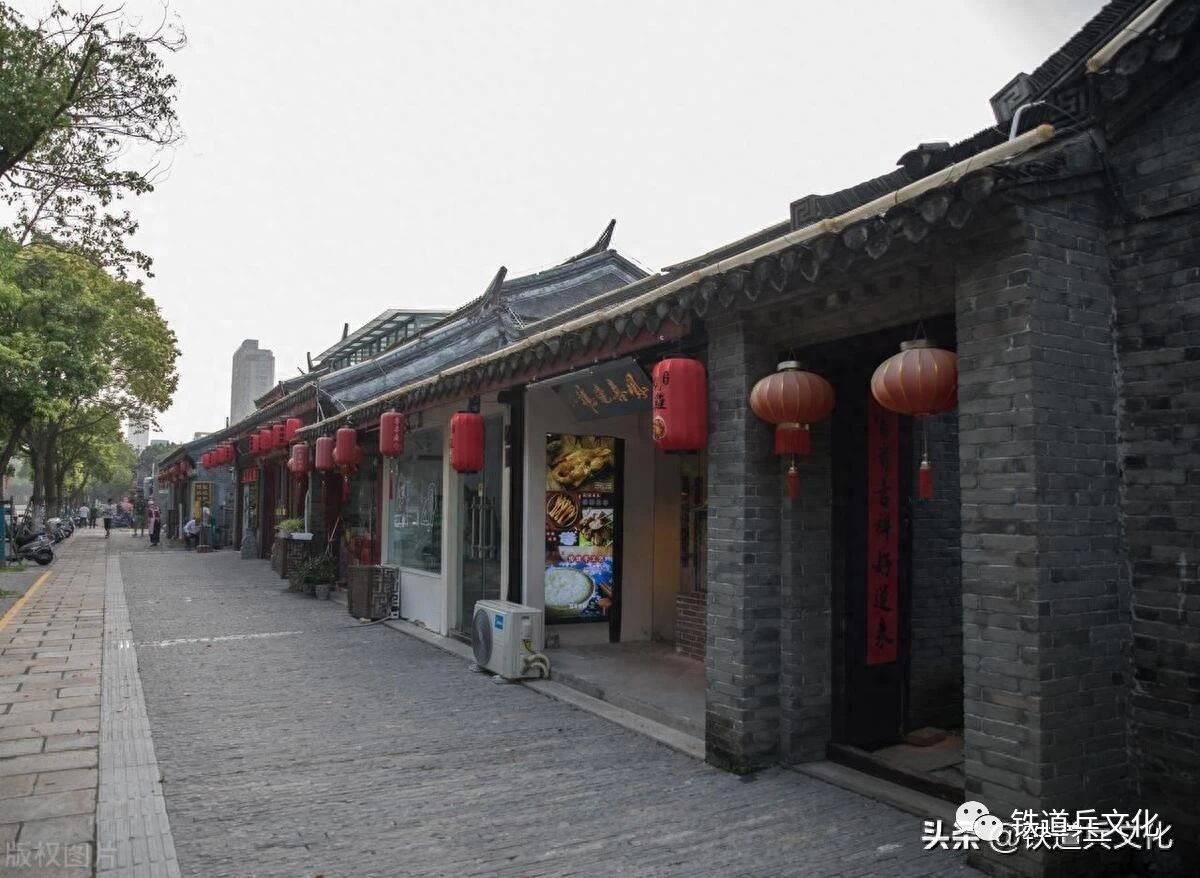
我家屋后是白蒲市河——运盐河,夏天吃饭之前,父亲到河里挑一担水,分别到入洗衣的大圆木盆、洗脚的高脚圆盆、洗脸的瓷盆内,放在炽热的阳光下暴晒,下午三四点钟水就很热了,夕阳下,父母将沉淀后的热水到入长木澡盆内,我就坐在长盆中,一盆水连玩带洗,爽歪歪,成就了我儿时洗澡的欢乐。这种洗澡方式在夏季可以适用,简单易行,每天就在屋后小院子里的夕阳底下洗。深秋季节,天气转凉就要转移到房间里烧热水洗澡了,那时候房间里没有空调、电暖气,也不到用煤碳炉取暖的季节,撩着盆里的水洗澡时感觉空气很凉,总是匆匆忙忙地洗完,抓紧穿上衣服,小心着凉。随着季节的越来越冷,为防止感冒,渐渐地就很少洗澡了。那时“冬季”十分漫长,从深秋到来年春天接近半年时间无法洗澡。脖子露在外面,是最容易脏的部位,就在每周洗头时顺便洗洗脖子,其它地方的污垢就任其发展了,晚上躺在被窝里摸摸膝盖上、胳膊肘上,厚厚的结满一层污垢。当姐姐们难忍了,吵吵嚷嚷要洗澡的时候,父亲这才烧好热水,把煤球炉拎到房间里,放上长盆让母亲给我们洗。姐姐们洗好澡后,母亲才把我叫进去敷衍一洗,边洗边说:“男孩子脏点没事,只要不到脏的地方去玩就行了。”煤球炉取暖,要防止一氧化碳CO中毒。我家邻居用煤球炉取暖洗澡时就中毒昏迷,不是发现及时,就发生大事了。父亲接受教训,我们洗澡时,父亲总是隔一段时间来房间看一下,通一次风。他一开房门,冷空气一进屋,我就大声嚷嚷:“冷,冷,冷……”父亲说:“冻不死呀,总比被煤气毒死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