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雾漫过书桌时,指尖总忍不住抚过叠得整齐的旧军装 —— 四十七年光阴流转,衣料上的橄榄绿虽已泛白,可青海的风雪、闷罐车 “哐当” 的轰鸣,仍像在耳畔打转。更难忘母亲围裙上没擦净的面粉,红帽徽被她的目光焐得发烫,那没说出口的 “别受委屈”,比任何叮嘱都沉,压在心底,成了往后岁月里的暖。
一、春风里的告别:那枚没说出口的牵挂
1978 年 3 月最后一天的上午,公社大院的喇叭把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的旋律揉进东风里,晒谷场的麦秸都跟着晃。我攥着新军装的衣角,指缝里的汗把布料洇出浅痕 —— 这料子比大队长老证爷带我义务劳动时穿的粗布褂软,却少了田埂上的泥土气,总觉得不贴肤。
老证爷把我、柏志平、陈宝祥往队伍里推,袖口蹭过胳膊,还是当年那熟悉的糙劲。队伍前头的闫排长,脸黑得像被高原太阳泡透的煤块,守侠姑娘凑过来咬耳朵:“俺家锅铲子都没这么黑!” 我笑出声的瞬间,瞥见人群后母亲正用围裙擦眼,围裙角沾着的面粉,是早上给我烙饼时蹭的 —— 她总说 “烙饼要烫面才筋道”,养我也这样,把牵挂藏在没讲完的话里。
出发前那晚我突然高烧,床头粗瓷碗里,守萍姑娘熬的姜汤飘着药香。母亲坐在床沿,手掌始终贴在我额头上,像块温温的老玉。天快亮时,我听见她跟邻居念叨:“这孩子从小就犟,到了部队可别受委屈。” 我赶紧闭眼装睡,怕眼泪掉下来,反倒让她更担心。收拾背包时,我悄悄把母亲纳的布鞋塞进去,鞋里的艾草漫着清浅的香 —— 后来在高原的雪夜里,这香气成了最念想的家乡味。
公社的欢送会在锣鼓声里开场,大红光荣花别在胸前,针脚细密得硌人。我们对着国旗宣誓,声音因激动发颤,像田埂上被风晃的麦秆。闫排长的嗓门比喇叭还亮:“把咱东庙公社最棒的娃,送进部队这个大熔炉里好好锤炼!”
登上解放卡车时,我一眼看见刚生完小外甥、没出满月的二姐 —— 她站在人群最前头,围巾被风吹得飘起来,为了送我,特意赶了几里路。车刚开动,我扯着嗓子喊 “二姐再见”,她使劲挥着手,眼圈红得像熟透的柿子。后来二姐在信里说,我走后母亲坐在我空床上哭了整整三天,几乎没吃几口饭。
二、雪地里的锤炼:那截冻硬的青春
蚌埠火车站的阳光格外刺眼,闷罐车像只厚重的铁盒子卧在铁轨上。我们顺着车门走进车厢,芦苇席的潮气裹着干草味扑面而来,天窗漏下的光里,尘埃像受惊的小虫乱飞。闫排长关上车门,只留一道窄缝透气。“哐当” 一声闷响,火车缓缓动了,我凑在缝上往外望:站台上的人影、远处的房屋慢慢缩小,最后缩成模糊的光点,直到消失在视野里。
车厢里渐渐暗下来,有人忍不住想家人,低低的啜泣声混着火车的轰鸣飘着。闫排长突然开口,声音格外亮:“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光荣的军人了!” 我们齐声应 “是”,那声音撞在铁皮车厢上又弹回来,满是热血沸腾的劲儿。夜里他教我们唱《战友之歌》,“战友,战友亲如兄弟” 的歌声轻轻回荡,有人跑调却没人发笑,大家都放低声音跟着唱,把心思融进歌里。
火车刚到哈尔盖站,车门一拉开,凛冽的风裹着雪粒猛冲进来,寒气直往鼻腔里钻,冻得人鼻尖发疼。跳下车的瞬间,视线先被晃了 —— 远处的祁连山像裹着层碎银,雪顶在阳光下亮得刺眼;近处的草原没返青,枯黄的草尖裹着薄雪,被风刮得贴在地面上。天地间只剩白与黄,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在寒风里发颤。
没走三步,身边就有人扶着车门弯腰呕吐;有人抱着头蹲在雪地里,指节攥得发白,声音发颤:“头疼得像被敲了闷棍。” 我也觉得太阳穴突突跳,每吸一口气都像吞进细小的冰碴,刮得喉咙发紧。裸露的手背没一会儿就冻得通红,连阳光都带着冷刺,落在雪地上的光反射回来,晃得人睁不开眼。这便是哈尔盖给我们的见面礼,壮阔里裹着凛冽,连风景都带着股考验人的硬气。
直到后勤部门送来军皮大衣,粗粝的皮毛刚裹上身,暖意就顺着领口、袖口往骨头缝里钻。我把大衣领子立起来,遮住半张脸望雪山,忽然觉出那片冷白里藏着的庄严 —— 风还在刮,可裹着大衣的身子踏实多了,突突跳的太阳穴慢慢松快下来。原来高原的暖,得靠这沉甸甸的大衣,一点一点裹进心里。
德令哈的风裹着冰碴子,我们刚跳下大卡车,寒气就往骨头缝里钻。刚到营地,鹅毛大雪就飘下来,落在军帽上没一会儿,就积了薄薄一层白。新兵连的帐篷在风雪里轻轻晃,唯有军旗始终挺得笔直,那抹鲜红像团燃着的火。班长教我们叠被子,手指捏着被角,一下下仔细压出棱角,“豆腐块” 在他手里似是有了魂。我练了半个月,手指磨得发红,总算能叠出像样的形状,可离班长的水准还差得远。
队列训练时,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正步走的脚步声在积雪的高原上荡着回音。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头晕得厉害,但我咬着牙没松劲 —— 不愿被连长说 “不行”。投弹训练最难忘,起初我最多只能投二十米,连长皱着眉打趣:“这力道,扔出去先把自己炸了!” 我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心里憋了股劲,课间练、晚上也练,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也没歇。实弹测试那天飘着小雪,我深吸一口气,迎着风把手榴弹掷出去,看着它在空中划出弧线,稳稳落在四十米外的靶区,连长脸上总算露出了笑。
射击训练更磨人,我们趴在覆着薄雪的砂石地上,一趴就是两三个小时,寒风裹着雪沫往衣领里灌,手冻得几乎握不住枪。可我眼睛死死盯着靶子,心里就一个念头:必须打好。最后十发子弹打了八十七环,班长拍着我肩膀喊 “好样的”,那一刻,冻僵的手好像都暖了。
紧急集合最让人提心 —— 哨声一落,就得摸黑穿衣服、打背包,慢一步就落了后。有回一个战友没把背包打好,抱着被子往操场跑,雪粒子打在脸上,我们没忍住笑,他却红了眼眶。后来为了不落后,我们干脆不敢脱衣服睡觉,这事被连长知道了,在大会上批评我们 “投机取巧,没养成正儿八经的习惯”。我心里忽然亮堂:在部队里,纪律比啥都金贵。
三、年轮里的回响:那截不会褪色的时光
新训一结束,我被分到哈尔盖仓库当通讯员。跟我同批从四联大队入伍的还有三人,她们都去了装卸班。没过多久,陈宝祥被选去学缝纫机修理,柏志平转去学油料管理,刘广云也调到了保管班。有时看见战友去学开车,我心里难免羡慕,但也清楚部队里没有不重要的岗位 —— 无论守在哪里,都是为国防事业出力。
仓库迁去德令哈后没多久,我也去了保管班。新仓库紧挨着火车站,在岗亭里站着,抬眼能看见火车进站,耳朵能接住鸣笛声,倒给寂静的营区添了些活气。轮到我站岗时,背上挎着半自动步枪,沿着仓库围墙慢慢转悠。夜里的风格外硬,刮过岗楼的铁皮顶,“呜呜” 地像谁在低声呜咽。每逢这时,我总会想起母亲说的 “到部队好好干”,心里瞬间就多了股往前冲的劲。
后来处机关的战友在青藏线巴音河畔遭暴徒袭击,此后站岗改成两人搭档,还为我配备了全自动步枪。有天夜里飘着细碎的雪花,我站在两层高的岗楼上,寒风裹着雪花往衣领里钻,目光扫过漆黑的四周,最后落在铁路方向 —— 昏黄的路灯透过雪雾,在铁轨上洒下一片朦胧的光。忽然,远处雪地里晃过来一个人影,踩着积雪 “咯吱咯吱” 地走过来。我心里一凛,等那人近了些,大声喊:“口令!” 那人脚步顿住,空气静得能听见风刮过铁丝网的 “哗啦” 声,他却没有立刻应声。我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赶紧握紧枪托,手指轻轻扣在扳机护圈旁,眼睛死死盯着那人的轮廓,连呼吸都放轻了几分。过了几秒,才听见他带着颤抖的声音:“陈、陈班长…… 是我啊,木工班老林!” 我仔细辨了辨,才听出是林师傅的声音 —— 后来才知道,他修门窗错过了新口令传达,回来时才慌了神。
在高原的六年里,我学会了坚强,懂得了担当。当过团支部书记,做过设备科统计员,也因工作扎实立过一次三等功;战友们的欢声笑语、首长的关怀鼓励,都是最珍贵的回忆。每年过年,我们围坐在一起吃饺子,办联欢、搞比赛、看电影,即便窗外飘着雪,军营里也满是家一般的温暖。
志平与宝祥都是当年的下放学生。志平刚入伍没多久,合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部队,可军务科长找他谈话时说:“现在你是军人,肩上扛着责任,不能说走就走。” 他攥着那张薄薄的通知书,指腹反复摩挲着纸边,最终还是压下了求学的念头,选择留在军营。
1980 年 10 月,塞北的秋风携着凉意掠过营区,志平与宝祥从物资科、供应车的岗位上卸下军装,告别了朝夕相伴的战友,也告别了这片熟悉的营盘。我们送他们到车站,谁都没多说一句话,只是眼泪混着秋风,凉得人心里发疼。千言万语,最后只化作一句 “常联系”。而广云仍在物资科多守了一年哨位,直至 1981 年 10 月,才背着行囊,踏上归乡的路。
转眼到了 1984 年 1 月,百万裁军的浪潮席卷而来,我随部队集体 “兵改工”。那天,军旗下的风格外轻,我抬手敬了最后一个军礼,指尖触到帽檐的刹那,眼眶忽然就热了;当亲手把领章、帽徽从军装上摘下来时,胸口像被掏走了什么,连呼吸都跟着轻了几分。可我清楚,那段军旅生活,早已顺着年月刻进骨子里 —— 不是军装在身才算军人,那份当过兵的劲儿,早成了生命里拆不开的一部分。
如今我总爱取出当年的军装,指尖抚过衣料上的旧痕 —— 那是哈尔盖雪夜站岗时,领口蹭的霜花凝成的白印;是投弹训练时,衣襟磨破又缝补的针脚;连袖口那点泛毛的边,都还沾着德令哈草原的沙粒。每一道痕迹都像个小开关,一触到,青海的风雪就漫过来:母亲纳的布鞋里,艾草香混着高原的寒气飘;帽徽上的红星,还带着当年被阳光晒暖的温度。
这些藏在时光里的牵挂与坚守,早成了我生命里最沉的宝贝。那段在风雪里守着的日子,像首唱不完的歌,在心里一遍遍绕 —— 它教会我扛住苦、守住劲,让我能稳稳接住生活里每一个挑战,也让我懂,军人的底色,从来都印在没说出口的坚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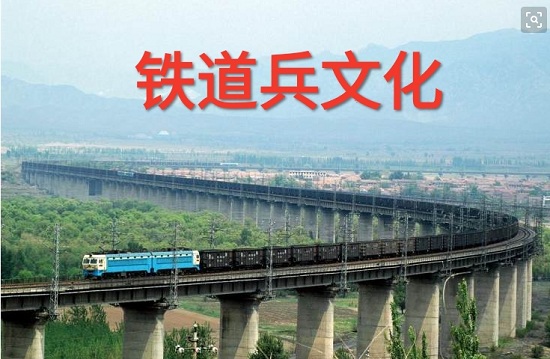
编辑:兵心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