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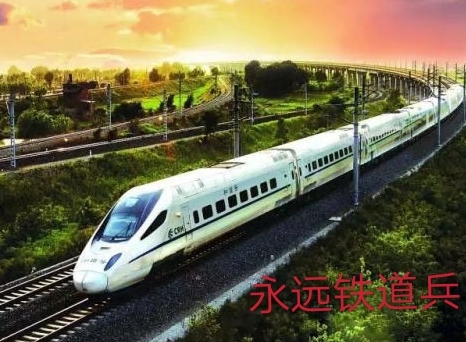
关角隧道的前世今生


朱海燕戎装照
关角,解读为登天的梯子
关角隧道,天路上第一道隘口
传说,杨戬是第一个要跨越关角的人
费九牛二虎之力,没有摸清关角的形体
退无可退,堂堂天神怎饮得下这杯苦酒
为泄心中之气,他把关角旁的一座小山
踢出一个洞。于是,“二郎洞”的神话
开始在这一带流传
01:41
1959年,铁路处在轻狂的青春期
想让绿色的火车,在青藏高原拉响汽笛
一批誓要打开历史一页的人
扛着十年家底的积蓄与精神
和西部辽阔的梦想与执着
来到关角,荒凉的大地上滚动起誓言的雷霆

季节未到春天,铁镐、风钻、钢钎
以及分离的上道坑、下道坑、掌子面,全部瘫痪
“下马!下马”的呼喊声,在他们头顶抱怨
冬天迎了上来,风雪汹涌地淹没你我
那是一个没有准备的退出
隧道掘进一半,进度被封在山里
西进的愿望,一夜间变成一句断头断尾的诗
登天的人,呼啦啦撤出高原
疼痛的语言,沒向遥远的拉萨漏出一句口风
为掩护一个国家的困难
关角这半条隧道,并没有死透
仅存的一口气,成为西进的根
成为山腹中的潜望,和蠕动的相思
作为没有死透的祭品,它还睁着眼睛
泪水挂在眼皮下面,瞳孔向东,默默呼唤归来的春风
没有文字的抵达,谁也不知这半拉子成果
等待的是泅渡,还是墓碑

1974年,一批修路人来到废弃的隧道
要让这首半死不活的诗,吐出韵律
衔接一个行吟西去的灵魂
向前挺进的时候,但愿不会遇到任何东西
关角沉然不语,这位生命的摆布者
在黑暗中布下重重杀机
死亡躲在隧道里,不是显露在阳光下
它无处不在地盯着人们,寻找机会
一天,它在与人类太多的博弈中突然走来
向一百二十七人张开血盆大口
塌方!塌方!非常熟悉的死亡曲调
在隧道里再次重复

死亡身旁,没有惊慌,没有悲痛
淡定与理智,让冲天的应对方式纷至沓来
指挥者高喊:“不许喊什么什么万岁”
不要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口号
节省体力,少耗氧气,才是生存之本
是的,在三千七百多米的高度
在四千米堵死的隧道里
氧气还不到海平面的二分之一
于是,他们把一生的日历,缩减成沉默,等待救援
把自己的生命,紧紧握进自己的手里

虽然,魔鬼紧咬着安全帽,扯着衣襟
他们还是于血雨腥风中,涅槃出人间大器
从死亡地带大踏步走出来
不是什么天惠的给予,而是智慧的大手笔
这支活命曲,成为天路上空前绝后的史诗

关角隧道,始终是心怀不轨者
既然不能阻止铁路前进,它就昼夜涌水
企图把火车的足迹埋进沼泽
让铁路受罪,永久活着过冬
00:08
天路,青藏高原的主动脉
追求它的畅通性,还要有细节的独立性
漫漫征程,岂能容关角隧道这个细节折腾
于是,在朝阳时代,在隧道之旁
又开劈一条新的关角隧道,长达三十二公里
从水底将铁路拯救出来,带着泥泞和一身水气

新关角隧道
至此,青藏茫茫高原上
过滤过无数生死与波涛的关角隧道
舞起彩虹般的身躯
潇洒出四千华里的大自由
二郎神被这胜利激动了
为观看这一景象
一使劲,爬到关角积雪的山顶

作者:朱海燕
作者: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协会员。
图片来自作者提供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