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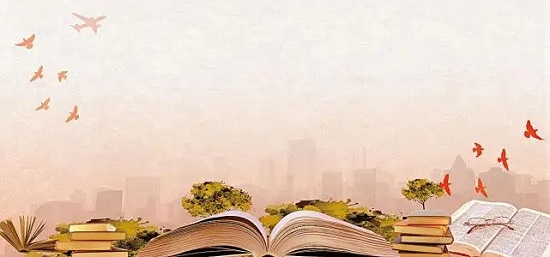
“眼热”“羡慕”,思来想去,觉得还是选择方言表达,更切合一位乡土学人的心境。
近日,我连读五部由博士论文修改的学术专著,李芳著《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朱振华著《扮玩:鲁中三德范村的年节生活》、李海云著《空间、边界与仪式传统:潍北的乡村生活》、张帅著《个人叙事与地方记忆:鲁中地区的颜文姜传说》、张兴宇著《梅花拳与乡村自治传统:冀南北杨庄考察》。
这几部著作的研究对象与宝卷多有相通相似之处,其理论、观点和方法可资借鉴。字里行间,时不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照亮我的思想,一些困扰日久的难题,瞬间解疑释惑。匪夷所思的是,开笔破题时,写作者尚且年轻,而对社会人生的洞察、体悟竟是那样地老道、深刻。田野调查、文献搜集所下的功夫,亦令人感叹!
这些年,博士、硕士论文读了不少,因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其感悟如滴水淋地皮,有痕迹而易蒸发。此次集中阅读,如同集束炸弹,一颗接一颗,密集投向心灵的炸点,强烈的轰炸效应,归结为两个字:“眼热”。
“博士”,词典释义,“学位的最高一级”。千万莘莘学子,梦寐以求,能如愿以偿者,几何?在笔者的认知里,凡读“博”者,无不才情横溢丶刻苦勤奋。倘置于历史的宏观视域观照,这些新时代的青年才俊,相较于我们这一代,可谓是生逢盛世、学逢盛世,一口气从小学读到博士,实乃人生之幸。
捧读论著,尤其是细读“前言”“后记”,发现这几位博士最大的幸运,是遇到当下中国一流的博导。“从论文选题、资料查访,到思路观点、措词表述”,(李芳著《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7月,第249页)每一个环节,都凝结着导师的心血。有位导师,从学生进门的那天起,便为其规划了未来十年的学术取向,乃至其后的人生轨迹。用有限的科研经费,资助学生赴外地搜罗文献资料,借出差之机,看望慰问学生,“请”其进馆子搓一顿,补充油水……每每读到此类文字,我的心头不由得一阵阵发热,尤衷地慨叹:做学问有导师真好!
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做学问,我的宝卷研究,只能自个儿孤零零地“闷头游水”,跌跌撞撞、扑扑腾腾地前行。我那几本小书,虽说也曾付出几番努力,几分艰辛,也有独到的体验和见地,但终归是“草根范”,与“学院派”的博士论文相比,“文”“野”立判。有时凝神遐想,倘若命运之神眷顾,有幸考研读博,我的学术水平、研究成果该是何等成色?正规而系统的专业训练,此乃眼热博士的根本所在。
然而,现实无情。于我而言,无高等学历、无导师引领,这是谁也无法改变、逆转的事实。由此想起一句名言: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年逾古稀,考研、读博的几率固然为零,就连投身名师门下也没指望。试想,有哪位学者收须发花白的老翁作“弟子”。好在研读博士著作,间接拜师,不失为走近博士、提升自己的捷径。
于是,那一本本论著便成为“教科书”。虽不能耳提面命,恰可以自觉钻研。不动笔不读书,习惯成自然。重点段落、经典表述,用红笔圈圈、杠杠,每有所悟,便在页面的空白处记下点点滴滴。甚至“糖炒粟子——现炒现卖”,运用耳目一新的观点,即时修饰自己的文论。
或许,此乃 “眼热”之真谛。
2022-10-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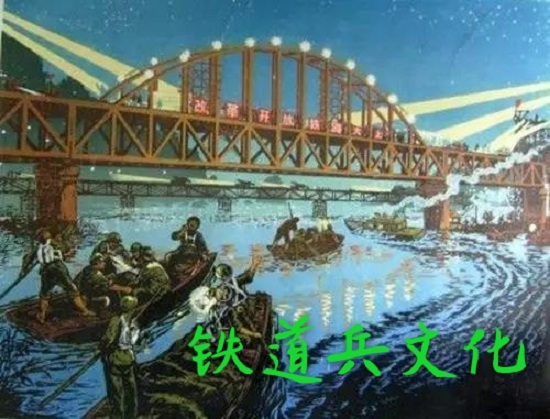
编辑:兵心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