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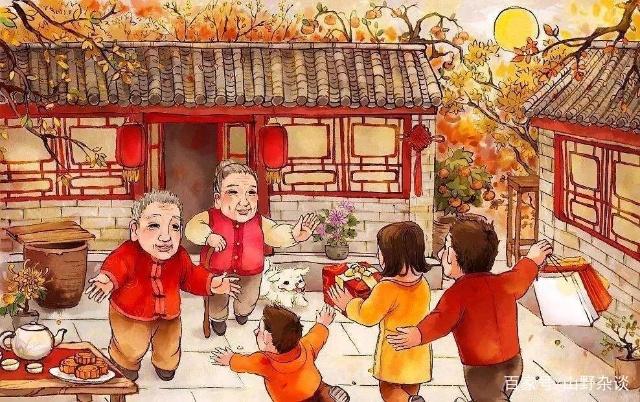
在我的家乡过春节,年味甚浓。一年里少有的闲暇,家家户户都忙着杀猪宰羊,灶台上和取暖的火陇上方,挂滿了各样腊肉、香肠,腊鱼、腊鸡。做月饼,打糍粑、炸园子、炒花生、炒蚕豆一样都不能少。为辞旧迎新做准备。尤其是大年三十晚上,一家老少通常围着火陇坐着,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俗话说:“三十的火、十五的灯。”守岁当晚,要将上好的柴火投入火陇,把火烧得旺旺的,火苗直往上串。人们期盼來年风调雨顺,红红火火。正月初一一大早,村子里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要互相挨家挨户的拜年,祝贺新年。“拜年、拜年,客气上前,粑粑米子不要,只要压岁钱”。这句儿时的顺口溜,在我的故乡原来很是流行。但小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念叨这句话去拜年,因为那时候我家的亲戚都不富裕。但是到了亲戚家里,零食必不可少。一般都有炒花生、炒蚕豆、炒红薯干或者麦芽糖制成的爆米花,一应俱全。按照家乡的习俗,毎年正月初二这天,是女儿回娘家省亲的日子,每到这一天,母亲就要带着我们兄妹,高高兴兴地回她的娘家走亲戚。儿时的我,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快快到来。那时候家里穷,缺衣少食,只有到了新年春节,才能吃上肉,有新衣服穿。我家到我外婆家穿心店子,其实并不是很远,但小时候却觉得路途特别漫长,尽管如此,一路上还是兴致勃勃地满心欢喜。
我是家中长子,肩膀背上背负着竹背篓,弟弟或者妹妹可以坐在里面,或者睡上一覚。我紧跟着母亲一步紧似一步,一直步行到母亲的娘家。外公、外婆早已过世了,舅舅的家便成了母亲必去的地方。背篓里装有节日的礼物,礼品虽不多,也不算贵重,但是全是当时拿得出手的、经过精心准备的、最好、最值钱的物品。用粗糙的纸张包裹成一小包一小包的,其实就是红糖、手工挂面、或杂糖之类的食物。甚至还有鸡蛋和油条。通常是走了一家亲戚后,这家亲戚会再添点儿别的什么东西,再往另一亲戚家拜年,虽然四位舅舅家相距不远,但每家都要住上一两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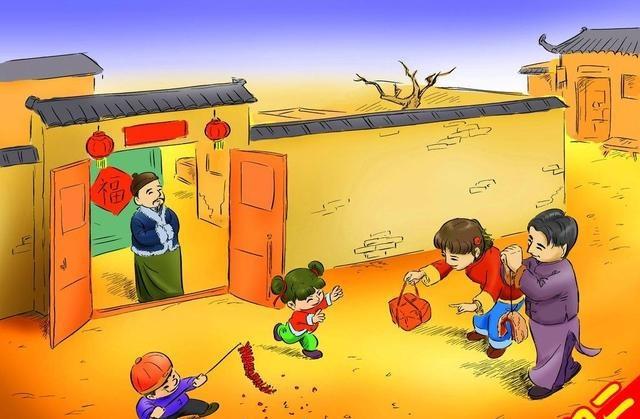
母亲的娘家,那时候叫穿心人民公社,是武汉经当阳通往宜昌的必经之地。到了穿心店子,再往前走,就是著名的佛教圣地玉泉寺了。二舅家住在通往宜昌和玉泉寺的交叉路口的公路旁。在这里要格外小心,因为离公路近,汽车往往飞驰而过,卷起的细石子在路上蹦蹦跳跳,汽车尾气排出的气味令人陶醉和向往。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能到汽车上坐一下该多好,不仅不用走路,而且还跑得飞快。那时候汽车不象现在这样多,一整天也没有几辆车通过,公路上马车和牛车比汽车多。每次看到汽车,一直目送它驶向远方,直到不见踪影为止。幼时的我没有坐过汽车,更没有出过远门,虽听说过北京、广州、和武汉,包括宜昌,在我脑海里就象在天涯海角。
我们每次走亲戚,都是先到二舅家,耀科表哥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读了很多书,从事着教书育人的工作,还曾经在我家附近的小学校任教,做过我的启蒙老师。我初上小学的时候,是在锦屏山下的一所破庙里,原来叫观音阁小学,因为背靠锦屏山,后改名叫锦屏山小学校。当时里面还供奉着神象,是当时当地最好的建筑之一。和尚们念经的地方,就成了我们上课学习的教室。平时我叫哥哥叫习惯了,但是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要喊老师,见面时还要鞠躬,低头行礼,感到特别的别扭和不习惯。大舅过世早,大表哥耀宽和二表哥耀运的家,也是必去的地方。四舅家住在靠近马路东边的村庄上。白的墙、黑的瓦格外分明,村里房屋较多、房子也大,房前屋后有大片的农田和池塘,远远望去,白茫茫一片。池塘里的水明镜似的,映照着蓝天白云,村庄上炊烟袅袅。田里的稻子早已收割完毕,可谷茬儿还残留在哪里。有时候能看到当地人用牛拉着石滚在地里辗压,感到很好奇,再用铁锹裁剪成一块块的土砖,待曰晒风干后,就成了上好的建筑材料。当时当地大部分的农家都用这种方法制作墙砖,不象我的家乡,是先将泥土和成泥再用木板制成的模具,将经过深度踩踏均匀的泥,用双手高高捧起,使劲砸在模具里、将泥按压拍打严实,再轻轻提起模具,每次制作都要将模具在水里清冼干净,再制另一块。等待土砖完全晒干风干后待用。那时候农村经济不够发达,实在买不起烧制的窑砖。与舅舅家虽然相距不远,真的是十里不同俗。但基本都是土法上码,自力更生。这种砖竟然也能盖房,住上上十年。这里鸡鸭成群,鸡鸣狗叫,村里不时传来家长呼喊着自家孩子的乳名"回家吃饭啦!"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小舅(宜昌人称“幺舅”)是有名的石匠,还会给猪看病,在我眼里是位了不起的大能人。耀江哥哥是老大,也是有名的乡村医生,他救死扶伤,解除群众疾苦,深受乡亲们爱戴和尊敬。方圆百里的村民没有不知道他的。耀珍姐姐,辍学务农,耀德哥和耀菊、耀翠两位妹妹尚小。耀学和耀科两位表哥,成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教书育人、率先垂范,两袖清风、为人师表,为国家和家乡培养了大批人才,硕果累累、桃李芬芳。一大家子人,非常热闹,其乐融融。(未完待续)

编辑:兵心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