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海燕 || 啼笑的婴儿
作者 朱海燕
啼笑的婴儿
近70年前,阜阳东北六七十里的地方与现在有很大的差异,那时,这一带没有一间砖瓦房,每个村子被有水的围濠围着,家家户户的房子,从不敢向围濠之外探头探脑,迈出半步。这样更显得村庄的孤独,田野的空旷,道路的遥远。多少个世纪走来的农耕生活,依然走在它原始的老路上,路边的水塘,芦苇丛生,野鹤横飞,间有野兔在路上窜蹦飞跳。文字定格在那个秋意浓浓的路上,那天,从一个叫朱庄的村子里走出几个人来,他们往西南12里外,一个叫小李集的方向走去。这几个人中,有两个妇女,一个青年男子,一个不到九岁的小男孩也跟着他们走着。那两个妇女,其中一位是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她也是另一位妇女的娘家嫂子,另一位妇女是男孩的姑妈,那位年轻的男子,便是小男孩的二叔。姑妈抱着几个月的婴儿,从出门那一刻起,这个不懂事的婴儿,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哭着,他仿佛知道这一天对他的生命会产生多么大磨难,未来的路是多么坎坷,他用哭声抗议着。若走完这12里的路程,他们这几个人的身份都改变了,姑妈将成为这个啼哭的婴儿的母亲,而母亲就变成了这个婴儿的大舅妈,青年男子现在还是婴儿的二叔,两个时辰后,他将成为这个婴儿的二舅。那个九岁的小男孩呢,现在是婴儿的亲大哥,不一会小男孩就变成他的大表哥了。
那一天是婴儿被送人的日子。他太小了,无力改变这一切,只能用哭声表达自己的心声。

尽管那一天的时间未能得到证实,但是大概可以确切地定为是晚秋的气节了。因为孩子出生于旧历的年三十那天,不到周岁的时候就被送人了,那么送人的时间完全可以把冬天排除掉的。因为冬天太冷,怕冻着这个体弱的孩子。无论母亲、姑妈或是二叔,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走路,寒风刺骨,手冻得也是受不了的。从这个细节推断,晚秋时节抱走这个孩子,才是较为合理与谨慎的做法。
如今,抱孩子的母亲、姑妈、二叔早已不在人世了,当年哭着牵着母亲衣襟不让把弟弟送人的小男孩也已是近80岁的人了。就是这些星星点点的细节,也是从他那八九岁模糊的记忆中流出来的,否则,婴儿送人这途中的细节,像一阵掠过的轻风,不会留下丁点儿踪影。
那一带农村,因为贫穷,又缺少文化,生活饥寒交迫的忙碌中,早挤掉了时间的概念,生命贴近大地,却不挨着时间,许多成年人,也可以说所有成年人,都不知道他生于何月何日,满足年龄确凿欲望的只是他们的属相,是鸡是狗,是龙是虎,十二属相是他们年龄定位的唯一的标志与记号,月份日期早已从他们的记忆中走失了。成年人如此,孩子们更是如此。
这个婴儿的姑妈,比他的姑父小七岁,基本可以这样推断,她是1927年生人,18岁时嫁给小李集一个姓李的男人,即在1945年的某月某日。一年后,她生下一对双胞胎孩子,不幸因病夭折了,此后的多种疾病她失去了生育能力。无奈,她从一个姓赵的家里领养了一个女孩,但仍觉得不够理想,她无法适应没有儿子的生活方式,于是,她想从多儿子的哥哥那里领养一个娘家侄儿,做她的儿子。
婴儿的父亲,那时已是拿工资的国家干部,可以这么说,即便家中有了几个孩子,他还是能养得起的,虽然家里不是特别富有,但比起纯粹的农民家庭,这个家庭已经是有着良好的声望和地位的了。妹妹想从他家抱养一个男孩,作为心疼妹妹的哥哥,不好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作为婴儿的母亲,她舍不得把自己的亲骨肉送给孩子的姑妈。这个工作不是孩子的父亲做通的,而是孩子的奶奶与爷爷和孩子的二叔与二婶。那时,婴儿的姑妈在小李集,虽不是声名显赫,但是那方圆十几里范围内,姑父的地位是不能小看的,他是解放后那个集镇的第一任支部书记,他的能力把那个具有几百年历史的集镇催发的无比辉煌与亮眼。

当初,朱家和李家这门婚事提起时,媒人说,男方是个穷苦人家,但是,这家是难得的好人,小伙子正直,有能力,将来能干成一番大事。岳父与未来的女婿见第一面时,说起种庄稼的事,摇楼撒种、扬场耕耙,小伙子样样精通。未来的岳父高兴的合不拢嘴,他说,没想到和我一样,是个精通土地农活的老把式,这人,这身板,这头脑,给人打长工都有出息。就这样,岳父把18岁的女儿许配给了25岁的女婿。
解放前,这位正直的女婿和一个要为百姓创造春天的组织有了接触。解放后,他分得了土地,分得了几亩宅基地和一个苇塘,加上他又善于经营土地和家庭副业。这样的家业在那一带极富吸引力。所以,孩子的爷爷奶奶、二叔二婶成天做孩子母亲的工作:“把孩子送给妹妹又不是送给别人,你是孩子的娘,她是孩子的姑,亏不了孩子。送给妹妹,是把孩子送进了福篓里、蜜罐里。自己的孩子不去,妹妹要别人的孩子,那家业,那树木宅基不都是人家的了吗。”这话成天在母亲耳边说,说长了说久了,母亲的心也被说软了。
起初,姑妈想抱走这家的老二,但老二已经3岁了,他知道送人的含意。只要姑妈来了,他东躲西藏,门后躲,床下钻,哭着闹着不愿意。姑妈是有心计的人,她抱走的不是娘家的侄儿,而是从娘家抱走一个“儿子”,孩子懂事了,不会对“儿子”这个概念认可的,孩子把她当成姑妈,不会当成亲娘。于是,她决定把只有几个月的老三抱走。
抱走那天,对孩子像打扮姑娘出嫁那样隆重,母亲给孩子做了一身新衣服,姑妈也带来一身新衣服和一些尿布。不懂事的婴儿,没有一丝记忆的婴儿,不知是命运之神的左右,还是其他,反正凭人们的认知是无法说清的,一醒来就哭,不停地哭着,又在哭声上路……

奶奶怕母亲与姑妈一路抱着孩子走得太累,就叫二叔也去送自己的侄儿。婴儿的大哥哭着闹着不让送弟弟,扯住母亲衣襟,走着走着,也就一同向姑妈家的方向走去了。
走到常营,婴儿一直在哭,母亲心软了,流着泪说“儿啊,你别哭了,娘不把你送人了,咱们回家。”娘转身向东北家的方向走,婴儿居然停止了哭声,露出一丝微笑。二叔说:“你说怪不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知道这个呢?”
就这样走走回回,回回再往前走,走到樊寨,婴儿似乎知道上当了,他没有往家的方向走,而是走向更远的地方,走向另一个家庭,他哭得更厉害了,娘用奶水喂他,他不吃;喂他鸡蛋,他吐出来。娘无奈,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哥哥拉着母亲哭着说:“别把弟弟送人,我不花钱,我省着饭给弟弟吃,把弟弟抱回家吧……”二叔拧侄子的耳朵,很严厉地说:“不许你这样说!”
就这样一路哭着,一路泪着,总算把婴儿抱到姑妈家,下身的棉裤全被孩子尿湿了,孩子的嗓子哭哑了,孩子无奈,把命运交给了这个家庭。
母亲和九岁的哥哥,没在姑妈家吃饭就返回了,出了姑妈家的那个集镇,母亲坐在地上又大哭一场。若干年后母亲说:“我能吃下那顿饭吗?那一口口是吃自己的亲骨肉啊!”
孩子到这个新的家庭,改变了另一种抗议的方式,他白天不哭,睡觉。每逢夜间就哭,哭得半条街都能听到。长大之后,一位他称三奶的邻居朱翠华说:“你呀,小孬孩,有名的哭夜郎,闹得四邻八家都不得安宁。”随着婴儿到达一个新家,十年之后,他将和我们这个民族一道,迎来一场巨大的灾难。而那场运动,其带来的苦难,竟让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痛不欲生。当年他的一路啼哭,难道是想避免或想躲开那场他不该经受的灾难吗?上帝,苍天,你难否告诉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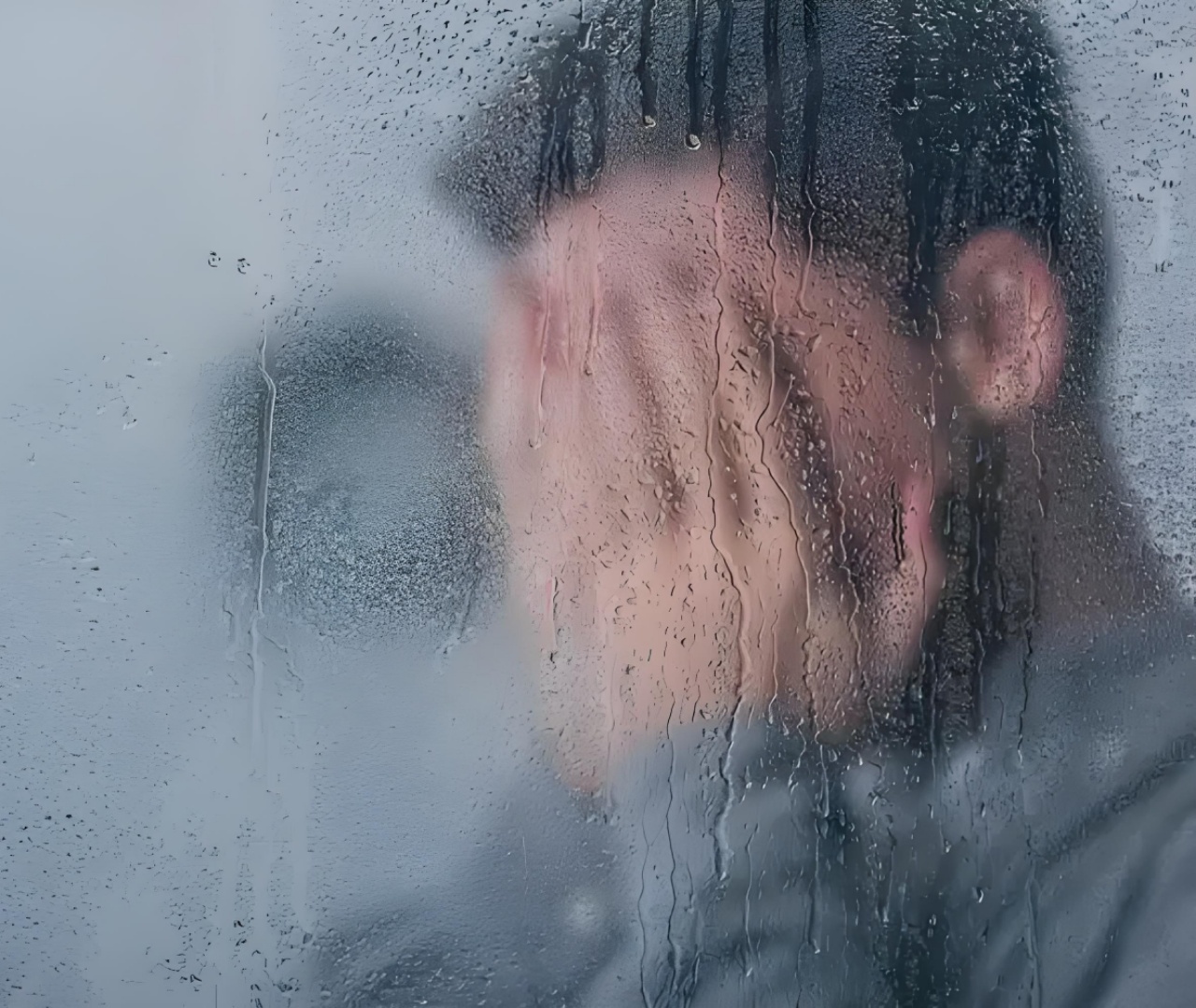
从到姑妈家那天起,这个婴儿吃着“百家奶”慢慢长大了,以至懂事之后这个集上的大嫂、大婶,见到他都会说:“你别跟俺家孩子磨牙啊,小时,你娘没奶,每天抱到俺家吃我的奶,你和俺家的孩子是抱一个奶头长大的。”
后来,婴儿长大后会写文章了,关于这一段经历他写成文章,发表在一份文学杂志上。一天,一位退休的小学校长到县文化馆,看到这份刊物,哽咽在喉,泪如雨下,久久心情不能平复。文化馆的人惊呆了,问:“朱校长,你怎么了?”他哭着说:“这是我弟弟写的,文中九岁的哥哥就是我。”说完,他伏案放声大哭起来……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图片来自作者提供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