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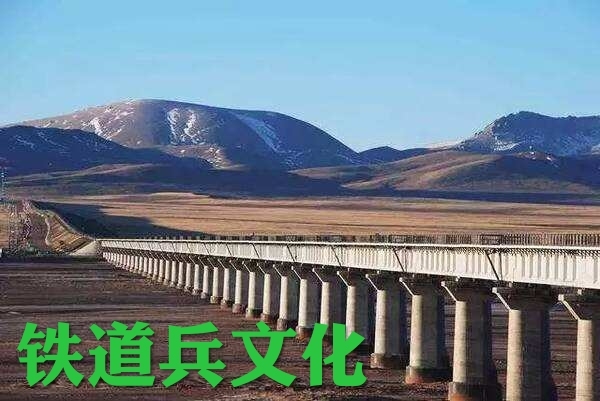
《西线烽火——铁道兵二团援越抗美纪实》
连载 第八章【纪念援越抗美六十周年】
《西线烽火——铁道兵二团援越抗美纪实》(连载)
姚尚明
第八章:中越友谊(4-7)
四、紧急献血
没有炮的轰鸣,没有警报声响,一阵紧急集合的钟声在连队敲响。各班跑步在“竹棚礼堂”列队报数,值班员向连长郑先才报告:“列队完毕,请指示。”
郑连长用洪亮的声音宣布:“听我的口令,所有B型血型的同志向左侧横跨一步,跑步站到十二班旁,依高矮次序列成一队。”严肃的队列里似乎出现了一阵骚动:“要我们这些B型血的干什么?”1968年入伍的一些B型血的同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郑连长深情地动员说:
“越南南方一位联队长(相当我军的一个营长)在越南北方接兵,得了急病,越方医院已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生命仍危在旦夕。现在,越方已把病人交给中国野战医院治疗。越方一再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医术很高明,相信中国同志一定会治好这位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的联队长。”
“现在这联队长急需输血”,郑连长说:“营长命令我连所有B型血的同志,在一小时内赶到764野战医院,为援越抗美,为世界和平做出我们的一点贡献。”
连长随后下达口令:“B型血的同志,立正——向后转,跑步走”。大家跑了大约十多分钟,在连队的山口,上了汽车,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行进很困难,大家一路颠簸,在车上你一言我一语,都说我们这批68年兵赶上了好时光,到越南已四个多月了,除了有少部分时间在铁路上修修补补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政治学习,美化环境上。有时公差,才能见到不少越南人。一心为越南人民多作贡献,可整天是学习、吃饭,打扫卫生,觉得非常内疚。这次要给越南战友输血,这多光荣,这多伟大,所以大家觉得赶上了好时候。可以直接地,面对面的援越抗美,为越南人民做贡献。
汽车一路颠簸,到了医院。大家坐在候诊室里静静地等待着,热情的小护士给每个献血的同志一杯冰凉的糖开水,一来解渴,平静一下心态,二来是为抽血作好准备。因为大家是新兵,又刚刚体检过,身体素质棒棒的。但为了对人的生命负责,医院按惯例仍进行了常规检查。结果很快都出来了,所去的十多个人,个个都可以献血。大家高兴得欢呼了起来。
战士彭松远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护士们来采血。和蔼可亲的护士们有条不紊地消毒,扎止血带,拿注射器,上针头,边工作边给讲:“在战时,献血是常有的事,为了抢救战友的生命,争得时间,血库设在每一个战士身上,随时都有为战友们献血的可能,没有什么可怕的。再说,每个人的造血功能都是比较强的,抽上300cc~500cc血,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何况我们这次是为越南战友献血呢。”
护士还告诉说:“我们医院每个人每年都要为战友献一至二次血,这很正常。”
殷殷的血液随着注射器慢慢的抽出,流到了输血袋里。
这次去的十多个战士,每个人都抽了500CC鲜血。据说,一个人正常的血液是5000CC左右,而十多位战士加起来的血,相当于正常人全部血液,换句话来说,越南南方联队长身上流淌的基本是中国同志的血。
后来听说,医院对这位联队长的治疗方案先进,供血及时,手术也相当成功,身体康复的很快。两个月以后,联队长完全康复出院,重返越南南方前线。对中国人民挽救了他的生命,他万分感谢,口口声声“嘎姆浓基”(感谢同志),“中国莫南”(中国万岁)。
几十年一晃过去了。这位越南联队长,现在你还好吗?
五、阮伯伯的功夫茶
陈双才副股长所在的先遣组到了克夫驻地,参谋长要他到附近了解社情,顺便探问有没有菜市场,但又要不惊动越方领导。他找到了村里的治安员阮伯伯,阮大伯大约五十多岁,中等身材,平易近人。见面时陈双才按越南的礼节双手合十叫声早谷!(你好的意思),他马上用中国话回礼你好!把他迎进屋,阮伯伯小心翼翼地从橱柜端出一套很漂亮的茶具,茶壶拳头大小,绿色花纹,镶着金边,非常雅致青翠,茶杯是贝壳经过精雕细刻制成,只有指头大,陈双才觉得很惊奇。阮伯伯告诉他,这茶壶是在二十多年前,一个中国梧州的朋友送的,茶杯是海防一位渔民亲戚给的。这套茶具充分体现了中越人民同志加兄弟的情谊。他已收藏了二十多年,没有用过,今天用来招待中国贵宾,真是派上用场了。他边冲茶边介绍说,他小学时学过中文,时间长了,现在只会写不会讲,他随手拿来笔墨,教陈双才一些简单的越南话,如吃饭叫庵公,喝茶叫翁厉,1、2、3——10莫(1)、海(2)、巴(3)——咪(10)。陈双才越学兴致越浓,边学边喝,由于阮伯伯的盛情招待,陈双才已忘了内外,无拘无束喝了二十多杯,不觉大钟已敲响了11下,这时才想起社情调查的事来,于是马上转过话题,问这个村有多大,他说有300多人,男的少,女的多,中年少,老小多,他说,听说中国部队要来了,村里人都很高兴,特别是50岁以上的老人都能讲几句中国话,会写些中国字。他还说,村里本来要组织欢迎你们的,但上面不同意,为的是要保障你们安全。他再三说,我们是欢迎你们入越的,他最后告诉集市的地址,但说没有蔬菜卖,因离省城远,村民只种少量自己吃。这样先遣组非到省城买菜不可了。
陈双才要起身告别,但阮伯伯却拉他再喝一轮功夫茶,盛情难却,他只好多坐片刻。这回慢慢品尝功夫茶,觉得特别浓郁甘香,这给他留下几十年的回味。在阮伯家里,陈双才见他们家用的大钟、煤气炉、火柴等都是中国货,难怪他对中国人的感情那么深。
陈双才在越南跨5个年头之久,所见所闻,所接触的越南人民,对中国同志都很友好,见面都脸带笑容,双手合十说声早谷!年轻的姑娘见到大家,就竖起大拇指说:“腊爪!”意思说,我们战友都很威武漂亮。
战争是残酷的,但人民的情感是美好的,一句话,一杯茶会使人久久感到心甜意乐。
六、一篮桔子和三个电话
“出国无小事,处处是政治。”这是援越抗美部队政治教育的一个经常性用语。出国人员“八项守则”规定不能随便接收礼物。但有些情况处理起来,却比较困难。
十连K185哨所驻在山头上,长年累月眼盯蓝天,观察空情。一有动静,立即发出警报信号。山脚下,住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只有一位60多岁的大爷。他的儿子到南方打仗去了。大爷身体有些小毛病。哨所的同志上下山常从家门前经过,一来二去就熟悉了。了解到大爷的家庭情况后,同志们一合计利用业余时间,帮大爷干点活,把砍柴、挑水,打扫卫生的事包下来。有时大爷出现头疼脑热,哨所的同志还通知连里卫生员给他看病。这一切使大爷从心里感到温暖。
秋天,大爷家的桔子熟了。大爷提着篮子走向桔园。摘了桔子来到哨所。说明谢意,放下桔子就走。同志们向大爷说明部队规定,不能接收。“不就是几个桔子吗?有啥不行!”战士小李见大爷执意放下桔子要走,就说:“我们打电话吧,请示连队,如果同意,就收下,好吗?”大爷同意,电话打到连部,回答是不同意,大伙再次向大爷解释。大爷只好提着桔子回去了。晚上,大爷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中国同志每天为他做事的身影总在脑海里显现。第二天一早,大爷又提着桔子来到哨所。这次,大爷不走了,拿着桔子向同志们的手里塞。我们的战士也来个缓兵之计,一人和大爷拉起了家常,一人向连队电话汇报,得到的答复仍是“耐心解释,桔子退回。”这次,大爷下了决心,不收下就不走了。于是,同志们佯作收下,大爷刚到家不久,桔子又送回来了。
看到退回来的桔子,大爷很生气。于是他把桔子一个个剥开,第三次来到哨所。看到大爷固执的神情,看到这一个个剥开的桔子,小李只好又电话如实汇报,这次连长王坤义答复:“收下吧,要多多感谢老人家。”
一篮桔子,三个电话,传颂着中越人民友谊的佳话。
七、赶猪途中
1967年春节临近,祖国人民关心在越南的英雄儿女。又送来了一批活猪。高机连分了5头,后勤处通知派人到寨湖车站去领。
连长罗克亮把这赶猪的任务交给了文书黄继贵和报务员李志泉。
他们两人到了寨湖车站,其他连队的猪都领回去了。后勤助理员一边帮忙用绳子拴猪,一边说:快点快点,趁天未大亮把猪赶回去,比较安全些。
李志泉考虑到文书有关节炎,就叫他赶两头大白猪,自己赶三头黑白相间的大花猪。二人一前一后,一手牵绳,一手拿竹条,不停地吆喝着赶路。
五头猪乘了几天闷罐车,一下车就像出了牢笼似的,撒起欢来。它们见水就喝,水喝足了,干脆将身子躺在水里不动了,不一会才爬起来,铁犁似的长嘴,见泥就犁,把土翻开,从中寻找着食物,格吱格吱地咀嚼起来,两人不停地大声吆喝,几乎把嗓子喊破,它们也不理睬,它寻它的,你吆喝你的。打它一下,开始还叫一声,后来任你怎么抽打,连叫唤也不叫唤了,好像知道自己早晚要死,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文书火了,拿起竹条,猛力抽打。竹条打断只剩半截,有劲使不上了。这时猪反而闹的更欢。他们在稀泥里打起滚来,一时翻过来,一时翻过去。文书和李志泉抓住一头猪的耳朵,企图把它拖上来,无奈,猪耳朵上尽是稀泥,滑的抓不住。天已大亮,二人又急又气。
猪不愿走,二人决定一头一头往回抬。他俩找来一根竹竿,好不容易把一头猪捆住,李志泉在前,文书在后。竹竿偏软,肥猪太沉,两人急步前行,竹竿随脚步有节奏地上下弹动。李志泉忍不住说起笑话:“这猪来慰劳我们多神气,先是乘火车,现在又坐“花轿”,咱俩抬着它,哼也不哼,屁也不放一个,像个自在龙。”
两人先把猪一头一头地抬出封锁区,放在公路边的香蕉林里,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往回抬。正在这时,一批敌机临空,他俩急忙把猪往树林深处驱赶。敌机似乎发现了目标,在空中盘旋。在这危急之际,忽然从林中跑出两位越南女民兵焦急地呼喊:“浓基,浓基,买买米,买买米。”(意思是同志同志,敌机,美国飞机)快去防空。两位女民兵帮他俩把猪拴好,接着拉着李志泉两人就往红河边跑。红河边有一个不小的防空洞,那里已躲藏着很多老百姓。女民兵带着李志泉两人刚跑进洞里,就听见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敌机把重磅炸弹,菠萝弹扔下来,香蕉林、山坡上、路基旁顿时火光四起,土石横飞,香蕉树连根拔起,冲向空中。防空洞内,这强烈的爆炸声,震得洞顶小土块不时的掉下来,落在人们的头上。老乡们随着爆炸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露出一副惊恐的神情。有两位年近70岁老妈妈挤到李志泉两人身边,伸出大拇指说:“感恩浓基,毛主席莫南。”(意思是:感谢同志,毛主席万岁。)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两个不知什么时候蒸熟的木薯,往他俩的手里塞。文书、李志泉非常感动,表示不饿,再三推辞,总算谢绝。
敌机飞走后,李志泉二人跑回原地。五头大肥猪无一幸免。一头被炸掉一只左后腿,死在弹坑,一头脑袋炸得稀烂,一头肚子炸穿,肠子飞散出来,头被埋在土里,还有两头都是后腿被炸断,倒在血泊中呻吟……
二人抬着一头死猪,飞快地回到驻地。立即将沿途遇炸情况向连长作了详细汇报。连长正焦急地等着他俩,见他俩抬着死猪回来,高兴地说:“猪反正要杀,炸死不要紧,只要人安全就好。”今天多亏这两位女民兵领你们去防空,不然可能就麻烦了。“人安全就好,人安全就好,”连长反复唠叨着这两句,又仿佛想起了什么:“文书,还是你两人去,再抬一头回来,现在天气热,其他三头连队一时也吃不完,就送给刚才帮你们防空的女民兵去处理吧!快去快回,多加小心,特别注意防空!”
文书和李志泉二人拿着竹竿,飞快地来到红河边的防空洞里,找到刚才的两位女民兵,打着手势,比划着将三头死猪送给他们处理,女民兵明白了意思,愉快地接受了高机连的馈赠,并向文书二人鞠躬表示感谢。文书说:“中越人民是兄弟姐妹一家人,不用客气。”女民兵跑回去一人立即叫来了六位年龄相仿的姑娘,七手八脚把三头死猪捆好抬走,边走边挥手,表示谢意。

由越方赠送给援越指战员的有胡志明主席题词的红色塑料牌。
文书和李志泉把另一头死猪也顺利地抬了回来!这赶猪途中的波澜,折射出中越人民的友谊。


1966年初,越南妇女送菜到部队。(马仁泉提供)

1967年8月1日前夕,越南永福省政府慰问部队,慰问品中有一个用“飞机毛”制作的象征中越友谊的杯。(熊泽海提供)
编辑:开门见喜